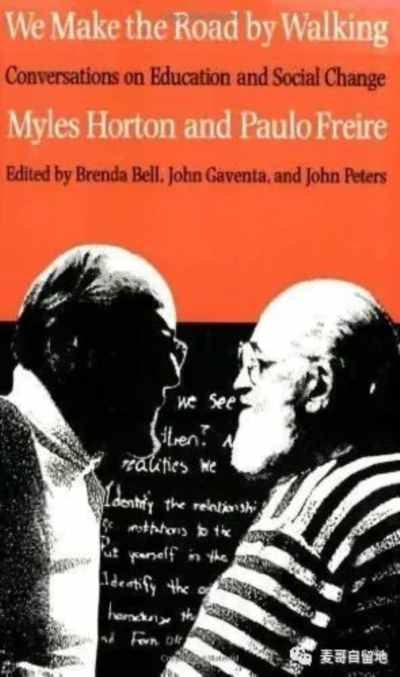有一天在一个同道中人的小群里,一个小伙伴如此“声讨”应试教育:
应试教育的结果不仅仅体现为一个人讨厌标准答案,还体现为一个人在讨厌的基础上失去辨别力。…… 1,应试教育带来读写无能,哑和盲同时存在。2,因为应试教育带来的伤害还包括让一个人懒惰和自恋(或自怜自卑),这个东西常常隐藏在明显伤害的下面,让她们认为祛毒的过程是“另一种集权”,让她们依赖和相信“温柔乡”来祛毒。弗莱雷就说过,“一直没有自由的人看到自由的时候,不是去拥抱它,而是害怕自由”。
她提到的这个陌生又耳熟的名字,弗莱雷,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查,乖乖,巴西人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和他的代表作《被压迫者教育学》在教育界和人文社科领域大名鼎鼎,据说是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人和作品之一。弗莱雷由此成了我提醒自己有多么无知的专用名词。
在另一条脉络上,从10月份研究丹麦的秘诀——“培智”(bildung),到其主要的教育载体民众学院(folk high school),再到民众学院在北欧之外的影响,我如此知道了格隆维思想和民众学院在美国历史上结出的最灿烂的果实,海兰达民众学校(Highlander Folk School)和它的创始校长迈尔斯·霍顿(Myles Horton)。这个过程也暴露过我的知识之匮乏,以至于把来到并影响中国已近百年的格隆维(Grundtvig)当成了自己发现的新大陆,译成了“格伦特维格”。
因此当这两条“无知批判”脉络交汇于同一本书的时候,这本书就成了我要优先阅读的,插到了包括《被压迫者教育学》在内的长长队伍的最前——它就是迈尔斯·霍顿和保罗·弗莱雷合著的《我们靠行走修路——关于教育和社会变革的对话》(We Make the Road by Walking——Conversations on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
Myles和Paulo(鉴于两位都是为平民教育奋斗终生的大师,以下就这么称呼他们了,亲切~)的经历既相似又颇为不同。两人都出生在中产之家,但青少年时期因家道中落而品尝过贫穷和饥饿的滋味——Myles是因为国家加大教育投入,同时要求教师具备足够资质,使得身为代课教师的Myles父母中年失业;Paulo是因为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对巴西经济造成的致命打击及13岁时父亲英年早逝。
他们都得到了父母用心的爱和呵护,虽然贫穷困顿,但充满自信,并未觉得自己“不如(insuperior to)任何人”。这一点对他们后来长期的“攻坚克难”生涯非常重要,用Myles的话说,“正因为我不需要把同情和怜悯浪费在自己身上,我才能对其他人充满悲悯。”
他们都既复杂通博(complicated & sophisticated)又简单天真(simple & naive)。Myles特别喜欢毕加索(Picasso)的名言:一个人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成长得年轻(It takes a long time to grow young. )。他们都推崇儿童的开放、自由、创造的天性,扼腕于这些天性被后天的教育和社会环境所扼杀,并勉力保持着自己的“天真”——Paulo的女儿Magdalena在洛杉矶第一次见到Myles时说,“他就像个婴孩!”
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如果较真一点儿,Paulo信天主教),从小具有自由平等观念和悲悯心(compassion),从青年时期就决意“走下三路”,即关注底层民生。都是天生的“挑战者”,从小学前后就产生了“质疑”意识,从目睹的个人悲剧(如Myles的父母不能任教后再也无法找到像样工作),开始质疑那些个体现象背后的体制(system)。
他们都早早在教会等社团里锻炼了人际沟通能力,特别是与底层民众打成一片、交谈、对话的能力(Speak with people,NOT to the people.)——这种融合和对话能力貌不惊人,实则非同小可,特别对于知识阶层来说,这一点后面会再次谈到。
他们都是学习派,是手不释卷的书虫,是思想开放、充满好奇心的终身学习者。Myles曾经和弟弟利用Sears & Roebuck公司的邮购规则的漏洞,“不满意就免费换书”,用一美金读了无数轮的书,直到两年后被邮购公司发现且不再为他们服务。他们都是行动派,从宗教信仰及相关活动经历里,建立了通过“行动”(act)和“做”(do)而不是仅“坐而论道”以改变世界的坚定信念。
他们还都极大地受益于第一任妻子——他们志同道合的最佳队友。Myles的“她”Zilphia善于用音乐、唱歌、舞蹈等艺术形式传递思想、激发学生的热情;Paulo的“她”Elza则一路提醒他忘记所学(unlearn)、注意倾听、用学生的语言、从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出发……简直就是“教练+队友”。Zilphia和Elza先后因病去世后,Myles和Paulo分别续娶的第二任妻子Aimee和Anna也是与他们继续结伴奋斗的同道中人。
(Myles的好“伙伴”,Zilphia Horton)
但他们的经历又颇为不同。Myles从中学开始就打工帮助家里,做过杂货店伙计、锯木厂和西红柿加工厂的工人,同时成为当地工会的积极分子。大学毕业后,他干了几年田纳西州学生YMCA(基督教青年联合会)的书记,然后先后进入纽约的Union神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学习,逐渐确立了通过教育促进社会改变的人生方向。影响他最深远的老师之一就是著名的神学家、社会思想家、社会活动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你可能没听说过尼布尔这个名字,或者不知道他是马丁·路德·金最推崇的思想导师、对二十世纪的美国社会影响最大的人之一,但你大概率听说过他的一段著名祷词:“上帝,请赐予我平静,去接受我⽆法改变的。给予我勇⽓,去改变我能改变的。赐我智慧,分辨这两者的区别。” 尼布尔的两本代表作,《人的本性与命运》、《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是洞察人的本性、意义,了解基督教义及人、神与社会、政治之关系的名作,对美国社会政治思维产生过深刻影响。
(海兰达民众学校校舍,1933年11月)
1932年,在亲赴丹麦考察了格隆维-克尔德式的民众学院之后,Myles走出了对理想教育模式的困惑,与两位伙伴在田纳西州的贫困山区Monteagle创建了海兰达民众学校。他们把格隆维倡导的平权教育方式(例如师生同吃同住同学、以对话和诗、歌为主的多元化学习方式等)引入到海兰达。海兰达成为他终生的活动基地,以这里为大本营,Myles先后投入到三四十年代的贫民扫盲、劳工权益活动,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和七八十年代的新劳工权益(健康、安全、经济人权等)中,并与国际性的活动家和组织联手,推动对全球化带来的人权等问题的反思和改变。
海兰达民众学校的高光时刻,无疑是为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输送了大部分中青年骨干。其孵化的公民学校(Citizen School)先后培养、启迪了十多万学生,大部分是来自基层的非裔美国人。来自亚拉巴马州的Rosa Parks就是在海兰达得到了思想启蒙,1955年她在公车上拒绝让座给白人而遭逮捕,引发联合抵制蒙哥马利公车运动,被美国国会后来称为“现代民权运动之母”。
(Rosa Parks和海兰达民众学校)
Paulo的青少年时代则相对平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相对单调”。虽然因为家道中落、迷茫和抗拒,他一度落后于常规进度4个年级,但他学会了与穷苦阶层的孩子们一起踢球、玩耍、交流。22岁时他才进入Recife大学的法学院学习,但毕业后却按照自己的心愿成为了一名中学葡语老师。3年后,他开始在Pernambuco州教育和文化部工作,边实践边为贫苦家庭开发一种低成本、低师资、快速有效的扫盲教育方法,一干就是10年。
1962年,他的方法(特意命名为“文化圈”而不是“扫盲班”)第一次规模化实践成功,300名甘蔗农工仅用了45天就学会了读写。彼时的左翼巴西总统若昂·古拉特(Joao Goulart)亲自考察Paulo的教学方法,旋即批准在全国范围大力推广弗莱雷式文化圈(Cultural Circles)。Paulo计划通过2万个文化圈,用2年时间在全国教会500万成年贫民读写。
1964年,美国CIA支持的军事政变推翻了古拉特政府,新政权认为弗莱雷的扫盲项目和教育思想有“颠覆性”危险,Paulo被捕入狱(《被压迫者教育学》即起笔于狱中),75天后获释,但被迫开始了长达16年的流放生涯。流放期间,他先后出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世界教会联盟(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的教育顾问,在美国推动了主流教育界对学制外教育形式(如海兰达等)的关注和认可,并指导莫桑比克等非洲葡语国家和智利等拉美国家的教育改革。
1980年,Paulo获准重返巴西,并加入工人党(Workers‘ Party),主管圣保罗州的成人教育,随后于1988年出任州教育部长。从1970年代开始,随着《被压迫者教育学》一书的流行,他的平民教育(Popular Education)思想和方法对世界各国(包括英国等发达国家)的教育界和思想界产生了长久、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纵观二人的成长和教育经历,似乎可以说Myles是先广泛再深耕,Paulo则是先深耕而后横向展开的代表。两种背景,两条路径,各有成就,使得他们的对话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左为Myles Horton,右为Paulo Freire)
在教育理念的形成方面,Myles和Paulo都从中学时期开始,对传统的局限于书本、课堂的灌输式教学方式(traditional schooling)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和抗拒,Paulo从自己的亲身经历里知道,读书必须让自己能联系到现实,“必须是出于热爱,像一件情事(Reading has to be a love event.)”;而Myles九年级时发现自己已经比任课老师更“懂”,但老师坚持说“你就要这么按要求写”,从此他开始了对这种”压迫性“(oppressive)教育的思想上的“批判”和行为上的“非暴力不合作”。
他们先后都受到圣经、马克思、杜威(John Dewey)等诸多经典著作和学者的影响,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马克思。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方法(Marxist Analysis)对他们理解社会本质(nature of society)——不同社会群体(狭义理解就是“阶级”)之间的关系、社会冲突 、经济关系——提供了分析框架,并开始学会辩证地(dialectical)看待复杂、多面的社会变化,面对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dichotomies)。马克思为穷苦大众而奋斗的热忱,其不懈地寻找实际地、结构性地改变社会现状的方法,也深深激励了他们。虽然,如Myles所说,“对他的预测和结论我并不太认同”。
有趣的是,Paulo还特别提到了马克思的教育观点: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也就是说,教育者必须接受并准备好在教育过程中自己受教育,从学生和在过程中一起学习,尤其是在成人教育的范畴里。
(Myles Horton走访当地农户)
Myles和Paulo都是“真实教育”的坚定信仰者。在他们的早期教育生涯里,都曾经“以传教士心态,带着我的经验、阅历、知识,来启蒙你”,但很快都发现学员们根本不在意、不理解、不感兴趣,“从他们的表情、动作上就看得出”,因而转向从学生的真实生活和真实问题出发,用学生习惯的语言和方式展开教学。
他们都主张“做中学”,而不是等待从上而下的构建之后才开始教学。只有动手时实践了,才能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这与杜威等学者的影响不无干系,与陶行知、晏阳初等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平民教育家的乡村教育实践不谋而合。
他们都坚信(成人)学生们每个人,即使是不识字的基层民众,身上都已经“颇有生活经历带来的知识,但他们往往不知道他们有知识、有能力”,因此主张“三位一体的学习”:学生从教师身上学,教师从学生身上学,学生们从彼此身上学。
由此,他们都发展出新的教育伦理:尊重人必须尊重他们的经历,而不是只是人格层面。Myles说,“要非常敬畏能把学生的经历之线拉伸多远”,以免拉过头而完全脱离学生的经验,导致学生无法把知识内化;“要从学生身上观察和学习”,并警告“很多自称弗莱雷派的教育者(educator),凭借自己假定的学生经历和知识”,实际上还是深陷于专家和权威视角。“要非常小心地区分教育者角色和专家角色”,教育者在自己已经有很多知识、甚至教育实践经验之后,还是要避免“出于帮助学生目的”的倾倒欲望和主观愿望。
(Highlander的工作坊,居中席地者为Myles Horton)
他们都认为最好的、甚至唯一可以有效的学习,是学生的主动学习。为此,教育者“绝对不能替学生做主和进行过度保护,那反而剥夺了他们学会自己做理智选择的机会”。Myles举了一个生动的生活场景作为类比,“怎么防止你的小孩子划船时溺水?有两种做法:把船扔掉、不再让孩子划船,或者教会他们游泳”。他又说,“你可以把马牵到水边,但不能强迫马喝水。”
Myles曾经作为辅导者参加一个工会的罢工策略会议。与会者面对问题陷入了束手无策的局面,而Myles坚持他们继续思考和讨论。一个心急的与会者用枪指着Myles要求他立即给出解决方案,但他宁可被打死也拒绝给出,坚持要他们自己继续思考。在另一个教师培训的场景里,Myles请来一位律师为学员们提供法律信息,但当好心的律师试图给出行动建议时,Myles赶紧抓住胳膊把他领出门去。
主动学习的根本动机是学生本身的强烈需求(needs),而不是锦上添花、不痛不痒的欲求,更不是教育者站在自己立场上的臆想。Paulo结合自己的挨饿经历这样说,“减肥时的饥饿不是真的饥饿,需要吃但得不到食物的感受才是真正的饥饿。” 民权运动中,美国南方非裔人的“识字通过投票权考试”就是典型的强烈需求,正是它促成了Myles主导的公民学校的遍地开花。
他们也都主张教学方式应该贴近民众的喜闻乐见,大量采用音乐、舞蹈、工作坊、对话等灵活方式,也不主张拘泥于固定的教材。孵化公民学校这个新项目时,年轻的主管教师Bernice Robinson找来一张独立宣言的海报作为第一节课的主要教学材料,这个所有学员都熟悉的场景很快勾起了他们的兴趣,引发了他们的分享和提问。
(Highlander图书馆前的小聚,左三为Rosa Parks,右一为功勋教师Bernice Robinson)
Myles认为,一个好的进步主义教育者必须具备四个关键素质:第一,热爱人民。第二,渴望帮助他们拥有你自己渴望拥有的。第三,敬畏人民与生俱来的学习、行动和自我塑造的能力。第四,尊重他们的经验和“活的知识”。Paulo完全认同,并补充了,“教育者必须是个富有安全感的人,安全感给予教育者去爱、保持好奇、保持谦卑、保持开放、乐于刷新认知(re-knowing)的空间。”
他们都强调教育者内心的自由,及环境对教育者的自由的宽容。没有体验到自由,就不可能理解自由。没有理解自由的教师,就不可能有自由的教育、创造性的教育。他们指出,教师最常见的恐惧,就是怕尝试新东西、怕出错,可是不冒险就不可能有创新。Myles在Highlander选择面向非裔美国人的公民教育的教师时,特别约定了一条规则,不要有体制内教学经验的教师,就是担心教师被已有的“范式”所束缚。1957年,他选择了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培训,但已有丰富的非裔社区经验的Bernice Robinson,她日后成为极为成功的公民学校项目的联合开创者。
他们都反对教育者应该坚持和自我牺牲。Myles说,因为从改造的事业中“感受到快乐,每天我都能得到自我滋养”。“我总是会因为学到了什么而激动、兴奋、快乐,教育就是总能让我学到东西的过程。” “我因为自己(从事教育)这一生活方式而感到满足,所以我从来没有感觉自己在做出什么牺牲。”
教育与社会伦理、政治实际上是不可完全分割的,因此教育者必须面对而不能逃避争议,必须有观点,“不能中立”(neutral);但同时不可强加自己的观点,而应作为一个共同学习者来呈现,提供相关的信息和视角。“决定权是学生的。最好的干预方式是提问(questioning)而不是演讲(lecturing)。” 当教育者提问的时候,“学生不会觉得你在干预他们,你会引起他们的兴趣,让他们心态开放,因为他们不知道,你之所以提问是因为你已经“知道”而且认为对他们也有价值。
Myles和Paulo的教育观念,当然也有一些微妙的差异。例如,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上,除了必须帮助受教育者主动学习这个共同点,Paul对教育者的权威性似乎有更多的保留,这多少有他成长于更为复杂艰难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子。他说,教育者要“保持作为教育者的权威性,同时又不压制学生的自由,并帮助他们学会思考和选择。” 而Myles对教育者的权威性避而不谈,更强调“强加”的风险。
对教育者的培养方面,Paulo特别不喜欢“培训”教师,他认为,技能和知识只是教师素养的一小部分,更多是不能“训练”的爱、热情、敏感性、尊重(学生的已有)、好奇心,所以只能养成(formation)。而养成是个漫长、需要耐心的过程,最终是教育者个人的演变,必须从外(个人经验和学习)到内(个人内心体验和消化),(面对他们的学生)再从内到外(呈现给和影响学生)。“最好的养成环境是既轻柔又沉重,既严肃又富有活力。” Myles对此似乎不太担心,我想这可能与他们两人面对的“教师”的特点有关——分别来自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
在教育的任务上,Paulo认为教育的任务不能仅仅是帮助产生主导性的意识形态,教育是一种超级结构,还肩负着“育人”的任务,即培育人“看清他们自己和他们所生活的世界, 并且能够去变革自己和世界, 从而拥有更加完美的生活”。而Myles根本就否定前者(形成主导性的意识形态)是教育的任务之一,它只是教育的可能的附带产品。虽然他的Highlander实际上帮助学员们形成了平等、平权、行动等意识形态,但学校的任务是让学生们意识到:自己是谁,值得尊重、有权利,相信什么,并要为之行动。
组织、动员与教育的关系。作为社会活动家,Paulo强调,“动员、组织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方式或过程,不能等到拿到权力再面对教育”。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也有类似观点,认为成人教育必须是一种参与式的探究、动员和组织。而Myles主张严格区分教育与组织动员,以防范在动员过程中受教育者学会的是“对人民的操纵”(manipulating people)。这个意见相左的点,再次反映了两人的背景差异,一个美国,一个巴西。Myles更警惕积极自由的滥用,这里有以赛亚·柏林的清晰身影。
在实践路径上,他们之间存在“应该在系统之内还是之外行动”的差异。Myles痛恨1930年代以降的美国普通学校(各种大学)的功利、官僚,机械的、脱离真实生活(不深究经济、社会现状和问题)的套装知识宣灌。他坚定地选择在教育系统之外做,因为他想颠覆那个陈腐系统,认为“在里面做只会美化和加强之”,而且新的思想和行动模式需要体制内不可能提供的“自由”。Paulo非常赞赏Myles为代表的系统外的实践,但同时更倾向于想办法在体制内行动,去从内部改革现有系统,虽然他也认可这么做的很难。这大概是因为Myles面对的社会治理机制非常稳定,几至不可撼动,而Paulo身处的巴西和第三世界国家大都正处于社会机制的激烈动荡时期,实际上他也确实得到过自上而下、在体制内实践自己的构想的机会。
教育,尤其是民众教育,不仅是长周期的,而且过程远非线性。Myles说,“这就像我们所在的山区,有野猪,有山头,有幽谷,Highlander的历史也有高高低低。但我们始终致力于找到一点点、微小的前进机会,不仅仅满足于苟活。在低谷期里,有人只是消磨时间地“挨”,而我们利用它为未来打基础……” Highlander的前20年、Paulo在Pernambuco州教育和文化部摸索平民教育的10年,莫非如此。
为什么选择做面向底层的成人教育呢?首先,Myles和Paulo有非常接近的初心:以教育为切口,服务民众,致力人性解放和更美好的自由平等社会。两个人的这种初心的形成,都是组合作用的结果:原生家庭影响、贫苦经历(“幸运地未被贫苦磨损反而变得更强”)、宗教信仰、先贤和哲人的影响、一路的生活体验……
Myles讲了一个田纳西山区的小学老师May Justus的动人故事。May在这片孤立无援的山区坚持做了10年的小学教育,也是Myles和Zilphia的两个孩子的老师。她成功地教给一届又一届学生爱、价值观、努力向前的动力,但有一天,她含着泪水告诉Myles,这些孩子一离开校园走进社会,“僵死、无望的社区就会很快把他们吞没”,使她多年的在校努力被消磨殆尽。“她是在说,社区是更有力量的,成人社会是更有力量的。”
Myles决定,“我想教育那些有能力改变身边的世界的人,如果他们想这么选择的话,而我也会影响他们这么选择。”
两个有趣的灵魂,两个做出相同选择但又走了不同路径的教育者。他们这场伟大对话的信息和内涵是世界性的。在对话的最后,Myles这样说:
"走进人民。向他们学习。和他们一起生活。爱他们。从他们知道的开始。用他们已拥有的东西建造。但是当工作完成时,如果人们会说,‘是我们自己完成了这项任务’——这才是最好的领导者。”
然后他问在场的人知不知道这是谁的话。采访者说,“你和Paulo都完全可能写下这样的语句。” Myles笑着说,“这是老子( Lao Tzu)公元前604年的话。当然这是意译过来的,但这思想与Paulo和我几乎完全一致。是不是很奇妙?”
附注:“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犹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 老子 《道德经》
「 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