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钟雪萍,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兼中文部主任,旅美学者,著有《Masculinity Besieged》、《Mainstream Culture Refocused》;研究范围包括:(中西)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与思想史,(中西)文化研究及其历史,(中西)女性主义理论和批评及其历史,
在会议议程上,我发言的题目是“为什么反思‘革命与妇女解放’成了女性的专业”。我先说一下这个题目。
2005年我在《读书》杂志上发过一篇文章,题为《后妇女解放与自我想象》。提交时的题目是《后妇女解放与男性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刊出时“男性知识分子”被去掉。尽管如此,我当时的考虑仍是源于对一个现象的好奇,即,中国现代史上,有不少男性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呼吁妇女解放;不但如此,妇女解放更是作为重要的纲领目标之一,存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诉求和实践当中。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在研究领域,“男同志能干的,女同志也能干”这类集体化时期男女平等话语被质疑,在男性知识分子的视野中更是很快地被弱化了。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女性研究、90年代出现的性别研究,都伴随着一个男女分化的过程,即,“女性研究”和“性别研究”主要成为女性学者的研究领域。我当时感到好奇:如何理解这个变化?男性知识分子的撤出是女性主义的胜利吗?
十几年过去了,尽管这个现象依然存在,我自己的认识却发生了一些变化。
2016年,在上海大学召开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历史与现状”讨论会上,我发言的题目是《重温中国妇女解放的阶级性》。今天发言的题目其实是那个话题的继续。中国妇女解放的成功与其鲜明的阶级性直接相关,而这一关系直接来自于中国革命的性质本身。
刚才应星教授在发言中说,20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不同性质的革命,一次革命,二次革命,要联系起来看。这确实很重要。当然,最终成功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表现在它带来的民族独立和中国社会飞跃性的变革。对中国妇女解放的认识,关键在于对20世纪中国革命的全面认识,更在于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
我在这里提到的“革命”特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在此前提下对妇女解放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进行延伸思考,并对改革开放语境中出现的“性别话语”进行反思。
近年来,在国内学界,对中国革命——包括其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重要意义以及认识这些重要意义的当下性等等——出现了很多颇具新意的思考。比如蔡翔的《革命/叙述》,2010年在国内出版时引发了很多反响。这样的研究和思考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中国学学界都很少见,不仅打破了一直以来的对“十七年文学”要么丑化、要么搁置、要么简单描述的局面,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其“叙述特性”的深层次剖析,提出了一系列理解中国革命的新思路,包括如何理解中国革命的现代性、文化建构与社会改造的关系、革命后面临的危机,等等。我和纽约大学历史系的瑞贝卡·卡尔(Rebecca Karl)教授合作翻译了这本书。英文版本2016年出版时,引发了不小的反响。当然有很多并不愿意正面认识中国革命的人,在学者中也大有人在,而且男女都有。但是,只要是稍微愿意正视中国革命在世界历史中意义的人,就会承认国内学者在这方面所取得的突破。我们作为译者所感受到的反应,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蔡翔的讨论中,“革命/叙述”不可避免地包含对中国革命与妇女问题和性别问题的思考。我提《革命/叙述》这本书,是想说,其实无论男女,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学者,是不能不意识和认识到妇女解放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意义的,因为在中国革命带来社会飞跃性变革的同时,其解放劳苦大众的纲领,无论遗留多少问题和遗憾,给广大劳动妇女带来的变化是结构性的,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层面上还是在个人层面上,既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特征,又同时在全方位的变革上一直面对深层次的挑战。对妇女解放的诉求和实践与中国革命的特质直接相关,一方面妇女解放因此得以成为中国革命的重大成功之一,另一方面也显示出革命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包括倒退的挑战。二者互为历史关系,互为政治关系,互为辩证关系,其中共同的内在基础,是对社会结构变革和重建的目标以及主体变革和重建的诉求。
在海外中国学学界,尽管真正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高屋建瓴地认识中国革命尤其是中国革命的世界史意义的,仍属凤毛麟角,但相对左翼的学者,无论是否真正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也无论是同情还是反对中国革命,一般认可革命的现代性意义以及中国革命在中国现代历史中对改变中国所起的重大作用。
所以,再次强调,我今天发言题目中提出的问题,并不是想停留在男/女的问题上,而只是从这个(继续存在的)现象进入,提出一些想法。希望大家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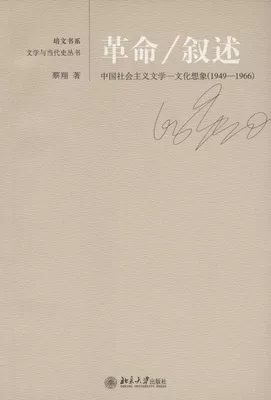
《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
:蔡翔
北京大学出版社
我先从两个(男性的)文本进入。
一个是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熟悉它的人都知道,那是鲁迅1923年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的演讲。五四运动提出个人解放、女性解放,走出家庭。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介绍到中国以后,在当时文艺青年中流传颇广。娜拉的出走被看作“现代女性”的觉醒。鲁迅则看得更为透彻,他认为娜拉出走以后只有两条路,不是回家,就是出卖自己的身体,别无其他选择。他在《伤逝》中,给子君安排的就是回家以及之后的死亡。鲁迅考虑的问题是,个体觉醒后会怎样?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个体面对的必然就是那个社会结构的逻辑,而这一逻辑必然继续殃及即使是“觉醒了”的个体。
纵观鲁迅的其他小说和文章,我们知道,鲁迅并不认为这只是那些觉醒后的女性所面对的命运。鲁迅不断指向的是社会本身(铁屋子)需要变革的问题。鲁迅当然不可能知道后来的革命具体发展成怎样,如今有很多人认为假如他活得更长,也许他自己会被他所期待的社会变革所吞噬,但是,历史毕竟是不能基于假设的(尽管假设可以成为历史学家们的学术游戏)。无论人们如何假设鲁迅本人会怎样,中国的革命历史证明,鲁迅的拷问是对的。从鲁迅的其他作品中,我们还可以读出,鲁迅所关心的,远非只是类似“娜拉”或“子君”这样的中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女性,他关心的还有“祥林嫂”“闰土”甚至“阿Q”,那些更为底层且处于散沙一片的大众。尽管人们认为鲁迅透过这些人物把批判的目光聚焦在传统文化上,但是,如果全方位地认识和理解鲁迅的话,可以说他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文化主义者”,他对文化现象的拷问是对社会本身的拷问,是一种疾呼社会要变革的拷问。

另外一个文本,来自20世纪80年代:1983年出品的电影《黄土地》。相隔上述鲁迅的演讲整整60年。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这部电影,因为教学的原因,我看过几十遍。作为电影,《黄土地》确实是一部经典。据说1983年在中国大陆上映时,它根本没有票房。同当时许多颇受欢迎的其他电影相比,这部被认为是“第五代导演”首次亮相的代表作,在国内基本没有票房可言,也没有引起当时文化界的关注。1984年在香港上映时,才在那里的文化精英中引发轰动,被认为中国总算出现了值得“国际社会”观看和认可的电影。随之而来的,是西方学界对《黄土地》的关注,出现了一些学术性的讨论,聚焦影片看似表现“革命”实则质疑革命的象征手法和象征意义。有意思的是,当时中国的文化主流被“伤痕文学”引领着,沉浸在对“文革”的控诉当中;而这部大多数人觉得“不好看”的电影却被悄然置入质疑中国革命本身的历史语境中。
影片的故事很简单,时间1939年,地点黄土高原(革命历史上的陕甘宁边区),只有四个人物:一位收集民歌的八路军战士(顾大哥)、翠巧、憨憨(翠巧的弟弟)以及翠巧和憨憨的父亲,片段性地讲述顾大哥作为八路军的文化工作人员,因收集民歌,借住在这个贫穷农民的三口之家,与他们之间的交流。在这部高度象征化的影片里,战士代表革命及其动员力量,翠巧和憨憨代表可以被动员的群众力量(尤其是年轻男女),他们的父亲则代表传统文化及其顽固的存在和影响。影片中,“革命的启蒙”最成功的对象是翠巧。当她得知父亲为还债而仍然要将她嫁人时,尝试着请求顾大哥带她加入八路军,却被不知情的顾大哥婉拒,说是要领导先批准。她被迫出嫁以后,决定逃跑,跟弟弟说要到河对岸找八路军。当弟弟让她等到河水不再湍急再过河时,翠巧对憨憨说“姐苦啊,姐等不了了”。于是,翠巧一边唱着顾大哥教给他们的革命歌曲,一边向对岸划去。但是,当她唱到“救人民来了共产党”时,那个“党”字没有唱出,即刻被湍急的河流声代替,随之而来的是站在岸边的憨憨大声喊出的“姐……”
在这个叙述里,翠巧的故事(也包括憨憨的)可以跟鲁迅的演讲(和小说)做一个(逆向)“互文”解读。在翠巧身上,也发生了一种“觉醒后”的出走;因为是发生在中国革命的历史框架里,她的出走象征革命对贫苦农民大众动员之后女性的“觉醒”和决定。但是,出走后的翠巧命运如何?影片似乎直接给出了答案:死亡,而且是唱着那首跟顾大哥学的革命歌曲,跟没有唱出的“党”字一起消失。如何理解这个处理?20世纪80年代,不少海外学者按着当时对中国妇女解放提出质疑的思路,认为影片就是中国人自己对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的质疑:中国革命似乎并没有给中国妇女带来什么变化,她们不是继续面对传统就是面对反抗带来的死亡。

电影《黄土地》海报
通过对这两个文本的“逆向”互文,我们可以看出,在质疑“革命”的历史语境中,妇女解放的发生,它的革命性,或者说在社会变革层面上的意义,被搁置被遮蔽(如果不是被完全否定的话)。这自然跟这一语境自身特有的话语逻辑有关,与知识分子的“现代话语”的回归有关。这是我下面讨论的重点。
《黄土地》代表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以及内涵其中的“告别革命”的走向。这一走向经由把革命与“传统”相勾连,进而否定革命的现代性,在逻辑上通向1986年出品的《河殇》以及所谓的回归五四重新启蒙。于是,“革命”等同于“传统”,“西方”等同于“现代”。
与“革命是非现代甚至是反现代的”话语逻辑合拍的,是一种对“普世现代”的想象,一种基于自由主义的“告别革命”的话语。联系到“妇女问题”,就是如何解释中国的妇女解放。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妇女解放的话语,很快被“回归中心”的精英知识分子占领,经由将革命定性为“传统文化”而受到质疑甚至否定。
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在张艺谋的影片里,那些巩俐扮演的女性角色。有批评者指出,张艺谋最初导演的“三部曲”(《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有“自我东方主义”倾向,即,按照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刻板印象呈现中国,从而强化西方的“东方主义”(即,西方中心)文化逻辑。但是,批评者少有提到的,恰恰是这些影片中同时隐喻着的“去革命”的话语,即,无视革命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革,把也许无法通过一次性革命而全然改变的文化问题,看作革命本身,予以否定。值得一提的是,这类通过表现女性质疑革命的隐喻手法,在80年代的男性文人——作家、导演、学者——笔下和镜头里似乎比比皆是。类似翠巧、菊豆、“四太太”(《大红灯笼高高挂》)等被“传统”摧残的女性,外加各种“马列主义老太太”形象,共同表示出一种“不到位的现代”,颇为巧妙地把“妇女解放”庸俗化、去现代化,因而不值得呼吁回归五四的知识分子待见。
进而言之,如果“回归五四”走向的不是鲁迅,而是“于永泽”一类,那么这一走向势必首先质疑来自“林道静”的挑战,质疑她对革命和所谓“自由”两者之间的选择。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
对妇女解放和革命的另一种质疑,来自西方学界包括女性主义学者。
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后来颇有影响的专著,定性中国的妇女解放不是“被推迟”就是“没有完成”。那么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应该怎么解释?对各种解释中存在的问题应该如何回应?其实国内已经有不少回应,基调是,对,确实仍然存在问题,需要反思,尤其是对革命中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存在的不足应予以反思。但是,在虚心接受的同时,如果要进一步思考,应该跟中国革命重新做进一步的勾连,在重新认清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再做反思。近年来,王玲珍教授对西方女性主义的“冷战”背景的分析和批评,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思考。
我想补充的是,也许其中缠绕的不只是“冷战话语”中形成的“西方”/“中国”思维定式,还反映出自由女权主义无法真正处理的“阶级”问题,包括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的阶级性。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问题相对无意识地也反映在80年代出现的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包括女作家和女学者)重点关心的“女性特质”问题上,认为妇女解放对男女平等的强调弱化了女性的“特质”和“异质”,纠结于“男女相同”还是“男女不同”等问题。在当时的语境中,这些质疑有它的道理,而且应该还是在接受妇女解放的前提之下提出的。她们的质疑指出革命话语中对两性关系和性别歧视的认识存在盲点,在与革命的大纲领紧密相关的一些小纲领及其实践中存在盲区和问题。对这些盲区和问题,女性主义的性别话语确实有打开批评视角的重要作用。
但是,今天回过头去看,需要重新认识的恰恰包括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接受层面上的历史语境:在“告别革命”的逻辑影响下,从“妇女”到“女性”多少有点类似西方70年代、80年代出现的“女性主义跟马克思主义离婚”的走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走向助长——我不是给男学者一个借口——性别研究本身性别化的现象,也助长“女性”被认为具有“普遍”内涵,而“妇女”则因其特定的政治内涵被特定化、边缘化(甚至丑化)。
进而言之,所谓“后妇女解放”的“后”,其特征之一,是“女性”这个相对去政治内涵的字眼的主流化。而其中自由主义(亦或资产阶级)的“原子个体”这一核心内涵,往往因为“社会性别”这一概念强调社会建构,一并被接受为普世的权利观。如此,这一变化成功地为接受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打开了认知层面上的绿灯,但对中国妇女解放本身的结构性意义,并不能提供革命现代和世界史意义上的认识。
指出问题后,在这里,我想回到“重温妇女解放的阶级性”这个话题,经由这个角度强调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妇女解放的目标和实践,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强调。
第一,林春关于中国革命的“阶级性”的讨论以及革命中国的“国家阶级性质”的讨论,值得一提。在她2013年出版的《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和当代政治》(China and Global Capitalism: Reflections on Marxism,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s)专著里,以及即将出版的一篇文章里,林春比较深入地探讨了从国家有没有阶级性这个问题出发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世界史意义。在资本主义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形式向世界扩张的历史中,中国在当时那样的世界范围内,作为一个被压迫的国家,它的这个地位的阶级性跟中国革命的诉求勾连起来,才能既理解中国革命的正当性、合法性,也能理解为什么革命的终极目标和具体实践在于,既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来解放中国的劳苦大众,也通过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解放中国的劳苦大众。
第二,妇女解放与解放劳苦大众相关,其阶级性取决于中国革命自身的阶级性。在这个大前提下,进一步思考和认识内在于中国革命的妇女解放与革命的大纲领和小纲领之间的各种关系,所谓“性别视角”才可能提供积极的批评和反思。刚才应星教授说,近年来对革命的研究中,存在注意材料的收集但同时又具有碎片化倾向,实证研究关注树木,但树林本身是怎么回事儿却不太关注。我在想,其实有些实证研究本身其实已经是主题先行,用看似新鲜的材料论证并不那么新鲜的观点。对妇女解放的研究中,是否也有这样的问题?就妇女解放跟中国革命的大纲领和它经常变化的各个时期的小纲领之间的关系而言,我发现,对小纲领之间的关系勾连比较多,但是对大纲领——也就是说到底是怎么样一场革命——的勾连似乎欠缺。
应该指出,20世纪中国发生的几次革命到底还是不同的。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它们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根本不同或者说相同的地方,就是说,它的“同”应该怎么去理解,“不同”又应该怎样理解,妇女解放的实践跟这一切又是怎样的关系,等等。这些方面的认识都很重要。要在结构层面上,而不只是停留在个人经历和经验层面上,做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我觉得它们的“不同”就在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强调的阶级特征:解放劳苦大众,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在多年“去革命”的话语影响下,这一点在不少人群中会被认为只是教条的说法、过时了的说法,但这种说法无法否定的仍然是革命本身的阶级特征,包括妇女解放本身的阶级特征。
第三,从“女性”到“妇女”,再从“妇女”到“女性”,“阶级性”内涵的变化。关于“女性”和“妇女”这两个词,已经有不少学术论说。但是探讨其中阶级性的,似乎不是很主流的研究。但是,在20世纪的中国,对这两个词接受的变化以及其中的思考,与革命的特质以及对这一特质的认识本身直接相关。
如果回到鲁迅,前面也提到了,他所关注的问题,不只是如娜拉和子君那些中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女性。今天,我们看他写的很多东西,发现他的思考对当下仍然有关联、有意义。他对女性的命运和中国社会的认识,关注的是对结构性问题的思考:只有改变中国,改变社会,才能改变性别不平等,改变广大妇女受压迫的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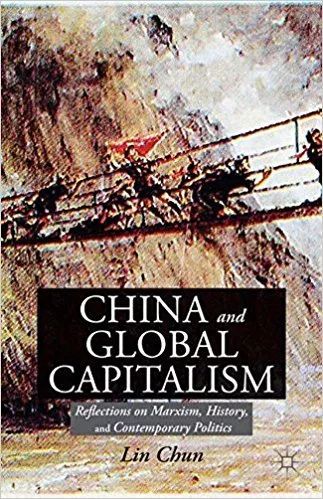
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著作,《狱中札记》
《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和当代政治》
林春 著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有过很多关于“妇女”和“女性”有什么不同的讨论。尽管在这里无法展开,但是我在想,如果把这两个词的用法和对它们的争论和讨论放进具体的历史语境里,它们本身的阶级内涵应该是很明显的。中国革命强调“妇女”在于其自身的阶级性;改革开放以后,“女性”的回归,看似回归“五四”,实际是没有了五四时期“女性”这个字眼的革命性。社会主义时期的妇女“走出家庭”“走上工作岗位”,确实并非源自女性群体和个体的抗争,并且因为它的所谓自上而下的即所谓“国家女性主义”特征,而被很多自由女权主义者诟病为被动的、工具性的(被国家利用的),而非“真正个体解放”的解放。这种观点在国内被很多人接受。但是,其中存在“个体为上”和工具主义的逻辑,基本无视妇女解放的阶级性,即,对劳动妇女带来的解放。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社会主义时期,不同阶层的妇女“走出家庭”以后,面对的不会再是鲁迅指出的两种“选择”;为什么中国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给广大劳动妇女带来的不仅仅只是有了工作机会,而且是参与社会和主体改造的意识和机会;为什么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才是个体解放的大前提;等等。
尽管变革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而且还会出现倒退,但就像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如果只用“女性”“性别”这些字眼,只是从“性别政治”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妇女解放的革命性,产生不出足够有力的分析。原因之一在于“女性”这个词本身的局限性:“她”与自由主义的“原子个体”同源,尽管承认社会建构性,但以“普遍人性”为前提,将“性别”等同于男性/女性之别,而其想象所基于的“男”和“女”,则无法超越作为主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本身的想象范围。
正因如此,在我看来,西方自由女性主义视野中的“女性”/“女权”实在难以反观中国革命中妇女解放的“身体政治”(姑且借用一下这个自由女权主义的说法)。难道妇女解放的身体政治真的只是“否定女性特质”“女人跟男人一样”“男女平等就是男女相同”而没有其他特征、表现和意义吗?妇女解放对新的“主体性”建构难道不是包含了很多层面的阶级性和社会性,包括男男女女都需要通过学习才能认识到的对传统的父系制度以及传统的性别歧视和习俗的批判和否定?难道结构性的变革中同时产生的文化和认识上的改造,就没有广大妇女自身主观能动地参与和推动?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这些年来出现的一些研究,对这些问题有了重新的思考和认识。中国的妇女解放的重要性和它在革命当中成功的原因,在于革命将其视为自身的一部分,即,将妇女解放视为改变社会、改变中国国家的各种各样的制度上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有机的部分。重新进入研究革命历史,就是研究自己的历史,为了理解当下,想象未来。
面对复杂的“变迁”,如何延续?
回到我发言题目提出的问题,质疑“女性化”走向,是想强调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的共同目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变革会不断发生,不可能一场革命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而且革命有时会走向它的反面。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不能因为一场革命当中没有解决所有问题,就认为这场革命本身是失败的。对妇女解放和革命进行反思的当下性,需要重新回到结构性问题的层面上,真正认识在什么意义上我们懂得,中国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革命。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需要也必须超越简单的性别区隔。谢谢大家。
「 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