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巴黎公社139周年
当飞机掠过这个城市的上空时,窗外瞬间耀眼一片。我立刻想起了NASA的那幅全球夜景图,那里有中国霓虹闪亮的沿海与黑暗沉寂的内陆。当时的我并没有想到,这次短暂的访友之行,竟会为我揭开这个城市华丽面纱下深埋着的泣血沉重的根基。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随朋友来到了这群HN工人中间。如果没有了解过尘肺病的可怕、如果没有见过他们迈上楼梯几步一歇的痛苦模样,光看他们因劳动而尚显健壮的身躯,我绝对不可能想到他们是一群行将就死的人!
我从中部来。我已经熟悉了家乡地图上那些详细的街道、繁多的工厂,虽然它们其中有许多已经破败停产,虽然它们昔日的主人曾经或正在走上街头——深圳这座城市,叫我头一个不适应的就是阅读它的地图:那上面有名目繁多的花园、嘉园、乐园,有数不清的广场、宾馆、酒店,但是当我把目光投向那些工业区、那些真正地在创造着这个城市的繁华的地方时,我却惊讶地发现,许多地方连道路都是不完整的!我诧异地指给我的那位朋友,他告诉我:这,就是这座城市的秘密。
“那时候,找到这个工作是很高兴的”
人均不过一亩左右的土地,种田再不能改善家里的生活,90年代,这群工人因想改变家中的困苦环境,从HN来到深圳,从农村来到沐浴开放春风的那个圈里。工人李zs今年只有36岁,但他来深圳干风钻已有十多年。97年刚过完春节,他就跟着村里的熟人来深圳打工。“都听说这里是特区、开发区啊,说这里很好,挣的钱又多。”38岁的刘r回忆说:“九几年的时候家里很穷,有4个子女,一个姐姐、一对弟弟妹妹,我家超支,所以我初中毕业就没读书了,没钱读书。来了深圳,一心就想挣钱”,“我93年结的婚,老爸身体不太好,得过糖尿病,老爸老妈都没有种田了,做不了什么事,就给我们照顾孩子。我们也不希望他们再做什么了。”
谈到曾经的收入,李zs说:“那时候,找到这个工作是很高兴的,能拿2、3千一个月,比种田多很多了。”“那时每年能带回家7、8千块钱,那可是一大笔钱啊。”尘肺二期的刘r说。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
“不用换啦!用胶水胶了就好了!”
工人们都说打风钻的活不难学,跟着先出来的下井打两天就会了。虽然说是危险工种所以工资高,但谁也不知道需要采取防护措施。李zs说,“那时候连给的口罩都很小,老板买的,紧得很,用十多个班才给换。平时我们说要换,他就说没有。这种口罩是橡胶的,边上一圈海绵会掉下来,我们要他换,他还会说‘不用换啦!用胶水胶了就好了!’”这种有橡胶、又有海绵的口罩已经算是最佳待遇,更多的工人使用的就是最普通的那种白色口罩,半个月一换、三十天一换——他们中的很多人“享用”了许多年。过去这种好一点的口罩一个4、5块钱,差一些的只要3块,但是老板都舍不得!直到07年才开始 “好一点”,“老板会买得多一些,一买一大箱,可以3个班换一个了”。这种“好一点”何其讽刺!因为根本就是一天换一个都是太少了的!工人说井下的粉尘特别大,在上面的人根本看不到下面的人。上来以后满脸是灰尘,全身是泥巴,眼睛上鼻孔里都是白色的尘土——有口罩其实和没有一样,一呼吸灰就进去了。上井的工人根本辨不出谁是谁,回忆起小学的课本,我忽然心中一凛:把人变成鬼的日子又回来了。
一般打一个井要半到一个小时,打完一个马上就去下一个,早上从7点干到11点半,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又要继续,只要不下雨,他们就一刻不停,从一个工地到下一个工地……双休日、节假日,在这个王国里除了老板一声令下别的什么也不存在。
“你情我愿”在这里不过是那些没有心肝的人薄凉的借口。工人们是承认当年的工资很高,可以拿到其他工种的一倍以上,即使“一般腊月二十几才回家”、但“到家里面带回这几千块钱还是很高兴的,有时可以拿回去1万多块”。只是他们心里都清楚:“老板吃我们吃得太厉害了,他自己心里有个底:他承包了多少钱、给我们多少他好拿得多。(拿这些钱)开支、生活费都我们自己出。”“工资不像工厂里按月结算,也没有确定的额度,都是老板说给多少就给多少,他想吞多少就吞多少。那时候给我们做这个拿25块钱一方,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还是25块钱一方,有的老板会给你30一方,但是物价涨了多少了?”“有时候老板会来工地看,他是来看爆破进行得怎么样——不是来看我们,建筑商是不会来管这些的。政府一般不会来管,管也只是来查看工地上的炸药晚上退回去没有,根本不会管工人。”
我不由想起我的姨妈,她当年从事的也是有毒有害的工种,上了年纪的她仍然身体健康。她说过他们那个国营单位规定特殊工种的工人拿退休金工龄一年按照一年半来算,不要说严谨的防护措施,一些工种甚至要求在岗几年之后就强制给工人更换岗位!我姨父的那个工厂一直都是政策性亏损的,因为工厂的建设本来就是为了支持中国落后的农业、提供低价的农机设备!“政治挂帅”就是要强调这是劳动人民的国家、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要人服从于利润和其他物质的刺激。当然,在改制的浪潮中,这些工厂纷纷都被摧毁了。我想,要是让他们看见今天新工人的工作生活状况,他们更要情何以堪呢!?朋友苦笑着对我说,他从来到深圳工作的那一刻起就明白了,因为他看见公司的账务上对应职员的工资福利那栏分明写着:人力成本。
“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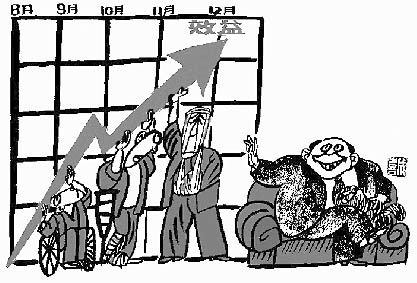
“你这个病还不符合住院条件”
他们中有不少人,上二层楼都要喘气许久,可是深圳市职业病医院给的检查说明却是:一年以后复查。有些工人去了其他医院,更多的则说:“别的地方也没联系,因为他们也没有说病,职业病医院现在都不给你认定了。”8月20日,工人徐zz在深圳市职业病防治医院去世。在不到半个月之前,这个医院的专业的权威的神圣的副主任医生向他宣布:“你这个病还不符合住院条件!”然后还没到三天,他就病危了。工友们把他送到最近的医院,折腾了一个小时后,医生束手无策让转送第二人民医院。在那里,他的喉咙立刻被打孔进行插管治疗,因为他的肺已经坚硬如石、再不能呼吸了!
拿起床头的药盒,我看到上面写着“清肺胶囊II”,这个药要30来块钱一盒,能减缓剧烈的咳嗽而并不能治病,就是这样他们也只有到呼吸困难了才吃2片,这样一盒可以吃上两个多月。工人们说这个药还没上市,是老乡从北京邮寄弄来的。“别的还能吃什么?就是那些确诊的人,医院也没给开药。”握着一瓶小小的“清肺胶囊II”,我的心中充满了痛苦,还没有上市的邮寄的药!经常有机会上网、看报的我们分明知道,这种药不是还没有推行的试验品、就是假冒伪劣欺骗钱财的……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人文关怀”
工人们不是没有抗争过。7月底,遭受到欺骗的他们去了一次市政府门前静坐。那天上午是烈日、下午是大雨,这是一群肺部严重有病的工人呵!那天的抗争,使得之前政府含情脉脉许诺的3万块钱的“人文关怀”变成了7万、10万、13万。但是这些钱,且不论被逃避的无可推卸的责任,这些钱,对于身染重病的工人们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发病了打一针要130-170多元不等,住院至少十天半个月下来就要花上好几千元,“发个烧马上就得打针、吃药,133块钱一针,不治的话就要发高烧了,到最严重的时候,真是山穷水尽了。所以林cw(爆破公司老板)他们是考虑的,他要认你一个就要认一堆啊,他肯定不会拿这个钱!”全心全意为资本家服务,这“人文关怀”说的实在太轻松、也太无耻了!
回想起8月10日前去参加深圳市政府组织的劳动关系确认会,工人们义愤难平:“去找他们,屋子里每次只让我们进5个人,他们一个老板一个劳动保障局的,把过程都录下来。进去以后,他就问我们,帮他做过哪个、什么时间做的,我们回答他,他们都不承认。”“老板他就是不看你,要不他就笑,就是不承认。出入证、出入卡都没用!我反问(追问)他,‘这个工地到底是不是你做的?’公证员就说‘啊,这个以后再说……’”“那个政法委的崔书记,他是读书人,我们是农民工,他那次说话我们一点也插不进去”“我们就跟他们对话不了了,没用了,他们本来就走这一个过程。”“他们给我们下一个圈套,办事处里都放了部队,外面马路的路边有两个豪华大巴、还有小车,里面都有武警,穿了警服拿着警棍。上次在市政府前面,也叫了9辆车,政府里面也有一车人。我们又不闹事,就是叫你解决问题……”“是没办法的办法了,只有跑到那边去找,你说不过他,也打不过他”……
“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它不过“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是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
“最痛苦的就是我们村11组,死去8个人了,还有13个,里面三期以上的有8个……”
城市里,工人们用血和汗建起了地王大厦,大梅沙,地铁一号线,海关大楼……
而他们的家乡,一个村的壮劳力死了将近一半……心里怀着这个惨痛的事实,我们跟随一部分工人回到了他们的家乡。HN省LY市导子乡……导子村、双喜村、洞中村、上古村……这里有如画的美景,这里加上风车和磨坊就是城市小资心目中的苏格兰农场!这里更有大把的土坯房,这里有的是老人、妇女、儿童,这里还有刷得粉白的两层排楼——村里人解释说,它们的名字就叫做“新农村”!
“如果知道会这样,谁会去干这个……”
“家里三兄弟(曹j、曹b、曹my)都得了这个病,叫父母怎么想啊……”
“他大弟弟(曹b)才37岁,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啊,看起来像一个老头子,三期了,脸都是黑黑的黄黄的,腿都瘦瘦的,人成了一个什么样子啊?!他兄弟有三个小孩子,老婆回娘家了,那边还有老人……他最小的女儿才4岁。把这么老的老人家、这么小的小孩子都扔在家里,叫人怎么过啊?……”
“现在的医院根本都进不得,药很贵很贵的,但是不吃药又不行,还要叫他们多在家里面休养,但不干重活。家里又吃什么呢?低保一年只有480块,好像是乡长叫他们回家来凭病历本才可以办的……”
“双喜村是最惨的,死了很多人了。我们这里也很可怜的,住在前面的是曹cs(音)的家,他前几年就这个病死了,老婆一直带着小孩在外面流浪……”
“他(曹xw)女儿现在才7岁,下半年上一年级,现在放暑假住在小姨家,平时都是她姑姑照顾她,她没娘了,爸爸又这个样……”
“这个是曹xq的妈妈。他的父亲前几年死了,他最小的孩子只有5岁,大一点的8岁。他妈妈又有病,你看,说话都不能说清楚,她是脑溢血……曹xq是大儿子,今年去复查的时候已经三期了,才41岁……”
“平时家里种一点小菜拿去卖,也吃不上肉。几个小孩一年上学加开销至少1万块,家里没有钱,小孩只能自己走路上学,每天要走6里多地、1个多小时……”
“这五年之间他(徐zq)还是在干活,给老板捻炸药、看炸药。他不敢给老板知道,走不动了就停下来歇一歇……他就是想多挣一点钱,家里有这么多孩子。怕老板不要他,他每次发病了就和老板说是感冒、发烧,问老板要一点钱去医院看看。去年10月病发得很厉害,一查就是3+了,实在干不了了……”
“90年,我丈夫39岁就走了,那时我才38岁,三个孩子才16、12、8(女儿)岁。我后来再没嫁过人,一直在家里干活,把三个孩子养大。大儿子(徐sz)2000年干不了活了,他17岁就跟着徐zh、徐lg去深圳打工,大概98年二儿子(徐sm)也去了……今年阴历五月初一两个儿子一起去深圳的医院住院,从最开始到现在看病一共花了好几万块。我的小女儿16岁就出去打工,那么多年挣来的钱都给她哥哥治病……结婚时家里连被子也没给她一套,家里什么都没有……”
“我的命好苦啊,不到一岁就没了父母。现在快六十了,就有一顿吃一顿吧。没有什么别的希望了,一天到晚干活,也不能吃好的。家里很少有肉吃,只是吃点蔬菜。我是穷苦人出身,没有好吃的,我就不吃,没有好穿的,那我就不穿。苦了这一辈子……现在儿子身体还不好叫我怎么办……”
“老公(徐yl)快死的时候,还是要去医院,好一点点了,还是马上回来,他舍不得小孩子。04年他走的时候,留下三个姑娘,一个2岁,一个3岁,一个9岁。我真的都不想活了,还有三个小孩怎么办?太难过了我朝他喊‘你把女儿都带走吧,留下来也养不活!’……他去了以后,连棺材都买不起,新衣服也没得穿,是他侄子买的棺材……本来三十几岁人,正当家了,几个小孩一起过幸福的日子,像这村里没打风钻的人一样……”
“我看见拣破烂的人,都活下去,也就一点点把小孩拉扯大。这几年我一直靠在深圳打工挣一点钱。第一年我出去的时候…肯定会舍不得小孩子,但是车费有又那么贵,到了过年,平时一百不到的车费连三、四百都敢要!小孩也给我打电话,说‘妈妈,你回来吧…’,我听了只能哭,我已经连着四五个年头没在家里过年了,要是我丈夫在,我肯定都会回来的……”
“老大14岁,读了初中,以后就不读了,家里没钱让她再读下去。我只有让她在家里带小孩——出去打工,哪里会要这么小的小孩。她很想读,老师也打了几次电话,可家里哪里有钱?她说长大了把钱还给我,她不想一下,现在生活都过不下去了,家里没有经济来源,她不知道我的苦……”
“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女儿才14岁,她说,‘我不读了,我要去打工,给爸爸(徐rn)看病!’这样她就跟人出去了……她现在在深圳电子厂打工,省下钱都给她爸治病。那个厂的工资不高,900块保底,然后再加班。她两个月往家里寄一次钱,自己每个月只花3、4百块。老师到家里来过5次要她去读书,我们家都没有电话,后来借了给她打,问她,‘你老师叫你去读书,你还读不读?’,她在那里哭了,最后说‘我不读’……”
“我担心爸爸(曹dg),我读高中也读不起。我知道出去打工很苦,但我吃得起这个苦。我也不知道出去什么地方可以打工,但我想给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
“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尾声
当我再回到深圳的时候,这个中心绚烂无比的城市在我心目中已经满目疮痍。我脑海里时时回响着已经死去的工人徐yl的妻子在她落满灰尘的家中对我说的话:“这就是我家里的房子,地上长满了草,灰那么厚,门几年都打不开了……我回来也不敢住在这里。……虽然说我们赚了一点钱,但那些人可发了。你知道吗,深圳那时候还像我们这边一样,草长得这么高,都是他们去盖出来的房子。”
这就是这座城市的全部秘密。被颠倒的世界必然要被颠倒回来。
相关文章
「 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