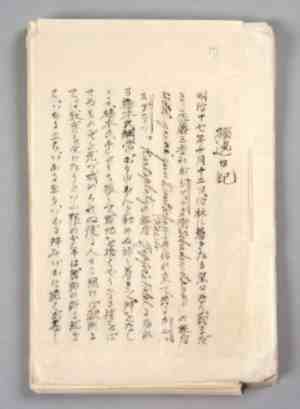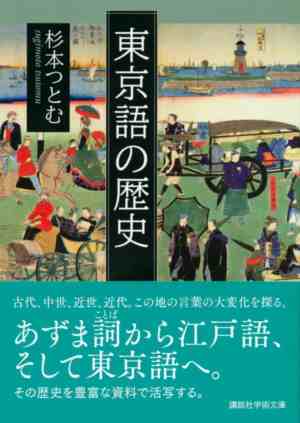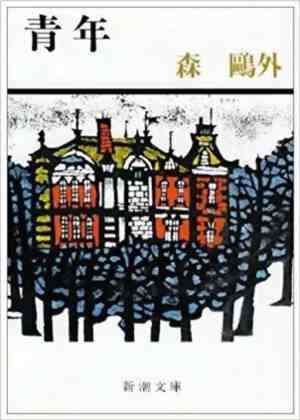y原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熊鹰老师《“使文成为文”: <言文论> 与森鸥外的国文构想》一文。
日本作家森鸥外在1890年左右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言文关系的评述,求索如何使经历了言文一致运动革新的“文”成为逻辑清晰、能描写人情事态的现代日本国文的问题。在森鸥外看来,近代以后言文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民族国家诞生后,甚至在帝国扩张时,如何创制出一套新的、“普遍”的文的系统,以及让经历了最初言文一致革新后的文成为文。他强调要经由不同文化的交锋来建立一种新的、混杂的,因而也是普遍的日文文体,并在同一时期以文语体创作了小说《舞姬》做以尝试。由此可见,面对“言和文”这样一个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普遍问题,他的国文构想无疑是一种文化译介交流的实践成果,以及对传统的再发现。
本文原刊于《外国文学评论》2022年第3期,感谢熊鹰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相关链接:
熊鹰|从“南蛮想象”到“南方想象”:现代日本文学中的异国情调及其与世界的联系
【建党百年特辑】熊鹰 | 亚非作家会议: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反殖民主义”问题
“使文成为文”:
《言文论》与森鸥外的国文构想
文 | 熊鹰
1890年4月,日本著名作家森鸥外在自己创办的文艺杂志《栅草纸》上发表《言文论》,对历时三十多年的“言文一致运动”进行评述。在《言文论》发表前后,森鸥外还陆续发表了《文海的藻屑》(1889)、《路功处士奇异的外形论者》[1] (1890)、《木堂学人文话》(1891)、《同一人的文的死活》(1891)、《学堂居士的文话》(1891)、《青年文学》(1892)和《言和文》(1892)等一系列文章,集中论述了当时日本的言文问题。[2] 同一时期,他还用文语体[3]——而非在此之前他已经开始尝试的言文一致体——创作了《舞姬》,并在1892年以后的十年中,用该文体翻译安徒生的长篇小说德语版《即兴诗人》,以期能创制出理想的国文。可见,1890年代是森鸥外最为关心日本言文一致运动的时期,也是他对尚未定型的现代日文形态进行摸索的时期。那么,森鸥外对始于1866年的言文一致运动以及截至1890年仍未定型的日本国文究竟持怎样的态度?
森欧外
由于看到1842年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失利,加之美国佩里军舰1853年的到日以及翌年《日美和亲条约》的签订,废除汉字、改行罗马字的改良之声开始在日本出现。1866年,前岛密就曾向当时的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呈送了《汉字当废之议》建议书。这一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也被后世的文学史从语言改革的角度定义为日本言文一致运动的开端,由此开始了一场长达近一个世纪的现代文体改革运动。在此之前,在贸易和外交关系上,日本江户是中国主导的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一部分,在语言上属于汉字圈;然而,《日美和亲条约》的签订打开了日本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与经贸的大门,如何通过改变日本的语言文字从而快速地加入新的世界体系,如何让政府的指令更好地传达给大众,如何尽快提高日本民众的读写水平而不被繁难的汉字所困,如何能毫无障碍地用文字记录语言,成为当时文体改革者们热衷思考的问题。起初,这场运动主要围绕“国字”改良,即在日文中去除汉字这一问题而展开。随后,学界又开启了有关文体改良的讨论。到1880年代后期,通过借用速记法,报纸、杂志等铅字印刷媒体得以将议会、学术演讲、授课内容、法庭辩论等广义上的“演说”记录下来,因而这一阶段被视为言文一致运动的确立期。此时,若林甘藏、坪内逍遥、二叶亭四迷、山田美妙等文学家都加入了有关文言一致新文体的讨论,尝试通过在句末引入“だ”“です”“である”等俗语语尾词进行文体改良。现有文学通史对这一阶段的文体改良运动总结道:“现在人们日常所使用的‘言文一致体’是由坪内逍遥提倡、在二叶亭四迷的《浮云》(1887—1889)及山田美妙的《武野藏》(1887)中首先尝试,然后再经过后来的‘小说家’们不懈努力才得以确立的。”[4] 与此相对,文学史也认为,在当时使用旧式日语的保存国粹的反动思潮中,专注辞藻雕琢之风的元禄文学[5] 在1889至1894年间抬头,同时也出现了和汉洋折中体、欧文直译体等与言文一致体不同的文体,言文一致运动遂进入低潮期。[6] 森鸥外的《言文论》及一系列有关言文关系的论文就发表在上述文学史所认定的言文一致运动的倒退期内,《言文论》所发表的1890年正值井上毅任文部大臣,标榜国家主义、提倡古典研究的时期。与森鸥外关系密切的落合直文等少壮国学者也在此时针对言文一致体的现状,提倡国文改良和美文写作。因此,森鸥外这一时期的写作被认为是言文一致运动倒退的典型表现。
二叶亭四迷
如果以言文一致运动为单一视角来审视森鸥外在明治二十年代的文学活动,往往会忽略他的国文观。1868年10月23日明治天皇即位,明治时代开始。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标志着日本确立了国家体制,一系列包括国文改良在内的国语运动由此展开。森鸥外的《言文论》正是站在国文改良的角度对业已进行了二十余年的言文一致运动做出的反思。明治二十年代后,旧式和文被国语取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7] 国文运动倡导者落合直文针对言文一致体者提倡的用和文俗语词尾进行文体改良的问题,提出要确立一种更符合语法规范的“新国文”。就在森鸥外写作《言文论》之前,新任外相大隈重信忙于与欧美各国签订通商条约,而日本国内正以侵略朝鲜为前提开展针对清朝的军备扩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启动了国家级的日语调查活动,同时还开始编撰“网罗性地收集当今之世日语,并以当今之世日语说明语义”(《日》:113)的《言海》。甲午战争以后的日本语言文字改革更是无法和“国语”“国文”这样的概念分开。言文一致运动和国语改革运动在日本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有着复杂的联系,写作于《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与甲午战争之间的《言文论》看似只涉及言文关系,但身为陆军省军官的森鸥外同时也在文中表达了他与落合直文相似的国文观。
1912年,身穿军服的森鸥外(右)和爱马。
1882年,森鸥外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进入陆军医院,1884年受到陆军省的资助赴德留学。在发表一系列有关言文运动的评论后,森鸥外于1893年出任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校长,可以说,他一方面是明治时代的文学家,在其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年轻的文人;另一方面,作为陆军省的一名军医和军官,森鸥外始终和现代日本的官僚体制以及帝国的扩张密切相关。1908年,森鸥外以陆军省军医总监、陆军省医务局长身份参加临时假名用法调查委员会,并代表陆军省发表意见。[8] 可以说,在作为日本帝国陆军省军官同时又身为作家的森鸥外身上清楚地体现了文学的言文一致运动与国文、国语的创制历史之间的复杂纠葛。言文一致运动在森鸥外这里并非自足的概念,也并非无足轻重。然而,正如本文最后一部分所要指出的那样,作为留洋学者,对于国文,森鸥外有着自身基于跨文化翻译的设想,绝非复古或国家主义保守思潮所能概括。那么,森鸥外的国文观与近代日本民族主义、复古主义和以本居宣长为代表的国学思想等各种思想流派之间有什么关系?他的国文构想和言文一致体的主要差异是什么?他的国文观又应放在何种思想和文化的脉络上来讨论?
森鸥外在德国留学期间
从森鸥外这一时期的文论中可以看出,到1890年,言文一致体的讨论已经从最初的国字改良问题过渡到如何创造出标准语、如何通过改良国文而使文成为文的问题。虽然都专注于如何创制出可以描写当代日本人情的现代日文,但森鸥外并不同意山田美妙等人在日文句尾引入俗语语格的做法。他在评述言文一致运动时,呼吁使用日文的旧语格,从而构建理想的新国文。具体来说,森鸥外一方面通过对言文一致体的思考与回应提出了理想的国文构想,即一种基于翻译、超越方言,且具有清晰逻辑和表意关系的普遍而理想的国文;另一方面,他也用自己的国文设想丰富了关于当时同样尚未定型的言文一致体的讨论。本文通过细读森鸥外在1890年前后发表的以《言文论》为代表的一系列文论,试图揭示言文一致运动与国文改良之间的复杂关系。
1
言文一致论的神话与森鸥外的“逆行”
森鸥外在《言文论》开篇即指出,被十八世纪的国学家们奉为经典的《万叶集》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日本并非像《万叶集》所说的那样“是唯一一个由言灵带来幸福的国家”[9]。短短一句对《万叶集》有关言灵论述“合理性”的质疑为《言文论》定下了整体基调,表明它与十八世纪国学者以语音研究为基础的国文论不同,也暗示了《言文论》与日本国学及国文学者之间的距离。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森鸥外及其同仁将他们自身提倡的国文称为新国文。
与普遍关心声音问题的国文学者不同,森鸥外在《言文论》中指出,本来韵文是为了歌唱和舞蹈而创作的,诉诸耳朵;而散文是为了阅读而创作的,只诉诸眼睛和心。在极端的意义上,音调在散文中没有丝毫的用武之地,若诉诸耳朵的韵文可以不使用新语格,那么诉诸眼睛和心、为了阅读而写作的散文也没有必要使用新的语格(详见「言」:82)。这里森鸥外谈论的是用来默读的散文和小说文体,即他后来所说的不适合朗读的“无声的文字”。[10] 森鸥外不仅不关心国文中的声音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反语音中心主义的。他清楚地指出:“虽然世间也有人听到言文一致的名字就觉得文即言、言即文,但言文一致只是采用今言而已,其本质则为俨然的文章,是为了读而写的文章。由于是为了读而写的文章,所以能看出充分的语言淬炼印迹,这也是和日常会话不一样的地方。”(「言」:80)换言之,“文”虽采用今言,但并不等于今言。因而,在《言文论》中,森鸥外认为落语笔记[11]就俗不可耐,他也借西洋人到非洲大陆旅行时用音符记录非洲土著语言的行为来讽喻日本的罗马字学会不顾母语变革的历史,凡事必依据现在的发音记录语言的做法。
鴎外主宰雑誌。雑誌「国民之友」に掲載された、訳詩集『於母影』の稿料をもとに創刊された。文芸評論を主軸とし、次いで翻訳に重きが置かれた。誌名は「文壇の俗流にしがらみをかける」という意。鴎外をはじめ、S・S・S(新声社)同人の著作が掲載された。明治22年10月~同27年8月刊行。
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认为,十八世纪的日本国学中已经有了语音中心主义,佛教僧侣中通晓梵文的文学者们对用汉文所写的《日本书纪》和《古事记》进行语言学分析,试图找到古代口语中的“古之道”[12]。这在本居宣长那里达到了极致。因而,柄谷认为语音中心主义并不仅仅出现在西洋,日本民族主义的萌芽也表现为在汉字圈中把表音性的文字置于优越地位。[13] 正如上文所言,一般认为,言文一致运动始于1866年幕府时期前岛密所提出的《汉字当废之议》,在此语音中心主义的延长线上,还有日语假名学会和罗马字学会发起的一系列活动。但正如森鸥外的《言文论》显示的那样,近代日本国语改革所面对的问题并非单纯的语音中心主义所能概括。至少,在明治二十年代,仅从森鸥外的《言文论》来看,言文一致运动也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表音”运动。如《言文论》及同时代的相关写作所体现的那样,与语音中心主义相比,森鸥外更关心日文文法、语格、句子构成、标点、断句、分段等问题,即如何成文的问题。这也是当时山田美妙和二叶亭四迷等言文一致论者实际关心的问题。
事实上,森鸥外是反对复古的,他说:“模仿死文,无论其所模仿的文究竟是希腊、罗马、秦汉唐宋,还是奈良朝前后的文”,都无助于这些国家各自的国文发展(详见「言」:77)。不过,虽然森鸥外与言文一致家们一样反对写复古的文,但他也不完全同意后者的主张:在对如何写“今文”的思考中,森鸥外对当时的作家兼言文一致论者山田美妙等人的主张提出了批评,尤其反对他们将东京方言中的俗语作为新语格引入散文的做法。
以往的论述往往将森鸥外的这些观点视为言文一致运动的倒退,认为森鸥外撰写《言文论》的明治23年正处于文学史所描述的言文一致运动停滞期。例如,站在山田美妙等人的立场上,山本正秀就认为,从明治21、22年开始出现了保守的文章雕琢之声,保存国粹思想兴起,支持言文一致运动的欧化思想退潮,保守的文章观不承认俗语俗文的价值,因此言文一致运动出现了停滞。[14] 在山本正秀看来,森鸥外正是这股保守风潮中的一员,《言文论》中对山田美妙的言文一致体的批评是受到了始于明治22年的、文坛开始向落合直文等人的“保守的国文改良运动”转向的强烈影响。[15] 山本正秀虽然区分了森鸥外的《言文论》与当时其他言文论者之间鲜明的差异,但他完全没有考虑到言文一致运动不过是近代日本创制国语、国文历史中的一部分,而将言文一致运动当作一项自明的、本质化的运动。事实上,小森阳一就曾指出,山田美妙之所以提出彻底拥护“今日俗语”的主张,正是基于其对国语的充分意识,他相信帝国宪法颁布后,比肩于欧美国家的日本可以与过去的文明割裂,日本帝国的国语是要走向未来的国语(详见《日》:114)。山本正秀并未看到,无论是森鸥外还是山田美妙,他们当时都站在言文一致运动与日本帝国国文创制的交叉点上,只不过两者前进的方向不同而已。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柄谷行人对森鸥外与言文一致运动关系的评价则与山本正秀恰恰相反。在柄谷建立的“明治维新二十年后”的谱系中,森鸥外这种反对声音主义、反对复古,也反对文言一致体的态度,具有某些抵抗“现代文学透视装置”的意味,即柄谷认为“‘文学’的主流并不在鸥外和漱石那里”,而是从其后通过言文一致体建立了日本现代文学中的内在性的国木田独步的路线上发展起来的。[16]对于这一时期森鸥外的写作主张,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如此评价森鸥外在《言文论》同一时期创作的《舞姬》:“在《舞姬》中,通过现在的‘余’来回顾过去,这样的视角[透视法]已经确立起来了”;但是,“鸥外分别使用了多种表示过去的语尾词。可以说,正因此他得以回避了言文一致”,这与山田美妙等人的语尾处理方法不同。[17]这里,柄谷所谈到的“分别使用了多种表示过去的语尾词”的写法,正是森鸥外《言文论》中日文书写主张的体现,即他拒绝山田美妙等人所提出的在语尾使用“た”和“です”等俗语新语格。简而言之,反对文章复古的森鸥外却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使用了能够表示多种过去的日文旧语格。柄谷的叙述着力于重构日本现代文学发现风景、树立内在的过程,因此在这样的历史中,森鸥外的地位便处于言文一致体的主流文学史视野之外;柄谷行人从国木田独步后来建立起来的文学路线中回溯了夏目漱石和森鸥外,将他们这种无法在明治二十年后期言文一致运动与国家体制相结合的历史谱系中得到解释的作家,描绘成是对这种体制有意无意的抵抗、怀疑或“尚未”,甚至是对现代性的抗拒。不过,柄谷行人的研究虽充分揭示了言文一致运动与国家体制相结合的历史,却没有讨论国语运动与国家体制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更进一步讨论言文一致运动、国语运动与国家体制这三者之间的张力。其实,像森鸥外这样在言文一致运动的历史中未能得到充分理解的作家,他和国家体制的关系恰恰能在同一时期的国语运动中得到更好的说明,因为言文一致运动与国语运动这两者并非毫无关联。
森鸥外的确在《言文论》里批评了山田美妙等人,称即使他们“只在散文里使用这些[新语格],我等也未能立刻承认将这些语格当作常格的必要性”(「言」:82);同一时期,他也确实用文语体创作了《舞姬》并使用了日文的旧语格,此后的翻译也使用了这种文体,虽然在此之前他已经尝试过在自己的文学翻译和评论中使用口语体及言文一致体的句尾“です”“ます”。[18]森鸥外的文体论和文体实验留给我们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用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来评价十八世纪以声音主义为研究主旨的国学家们和言文一致体这一近代装置形成过程中的日本文学,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处于这两者之间的明治二十年代的森鸥外的国文观?除了“不足”或是言文一致运动评价史上常常使用的“倒退”“挫折”外,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森鸥外反对复古却也同时反对声音主义及言文一致体的国文主张?
山田美妙
山本正秀只看到言文一致运动的历史,而忽视了它所从属的日本帝国国文与国语改革的大历史;柄谷行人则主要关注近代日本国语和国文与语音中心主义相结合的历史,因而,森鸥外的言文主张在他们各自的历史叙述中往往作为不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低谷或“尚未”而出现。本文认为,若要讨论《言文论》的意义,首先应该将言文一致运动和相关的言文问题放置到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家和国文的创立过程中去考察,将言文一致运动看作一个能容纳不同国语主张、内部充满矛盾和张力的装置,而不是将它绝对化和神圣化。下文就将具体论述森鸥外在《言文论》中所谈及的有关日本国文创制的几个重要问题以及它们与言文一致运动的复杂关系。
2
去方言的国文观
在《言文论》中,森鸥外坚持文有雅俗之别,认为极雅的文和极俗的文冰火不容,文需要打磨,是俨然的文章。但正如上文所说,他也反对文的简单复古,主张将今言直接变成今文,不再作复古的文。可见,雅俗的标准并不在古今。虽然主张今言,但森鸥外却认为今言未必雅,因而需要淬炼。
从《言文论》和《舞姬》来看,森鸥外不满的正是山田美妙等言文一致论者所提倡的俗语新语格“てにをは”,也即从东京方言进入日文及标准语中的语法规则。这一规则集中表现为对词尾谓语动词的时态及助辞“だ”或“です”的使用。森鸥外考虑的是如何在文中对话以外的叙述或描写部分雅致地使用今言而不使用方言语法规则,重新创造一种普遍的语言。他以德语文学举例:“现在的巴伐利亚,本该说ich schlafe(我睡觉),人们却说ich thue schlafen,但这种新的用法并没有进入文。我国的だ和です和这个也有些相像。”(「言」:82)在森鸥外看来,言文一致论者试图使用的由俗语语法规范起来的语言只不过是东京的方言而已,其地位等同于巴伐利亚地区的方言,不应该成为文的规范。
《舞姬》,载《国民之友》69号。
以东京方言为明治政府标准语的倡议正出现于森鸥外发表《言文论》之后。1894年,同样留德的上田万年发表了《国家和国语》,次年又发表了《关于标准语》等文章,提倡在东京语的基础上进行“人工的雕琢”,从而建立标准语。[19]国语的概念经常会因为帝国边界的不断变动而发生变化,并不能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当“国语”尚未在日本国内被整合完成时,“标准语”概念又作为观念性的“国语”在现实世界被提了出来(详见《日》:147),因此,在帝国边缘,标准语往往作为替代概念被提出。早在1880年,东京语是最好的语言而应当被学习的意识已经远播冲绳。掌握不好“标准语”已经成为非东京人的一大烦恼。[20] 甲午战争以后,标准语的确立过程和方言扑灭运动相结合,其主旨强调的是帝国的统合(详见『江』:54)。在此之后,所谓的“标准语”更加明确地指代居住在东京、受过教育的东京人所使用的语言。
上田万年在《关于标准语》中指出,德国标准语的基础是路德翻译《圣经》所使用的语言,这种语言的品位得到提升后,成为日后统一帝国的先导。[21] 德语的统一确实形成于1522年马丁·路德翻译《圣经》之后,但路德使用的是十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内的萨克森方言。当时各种方言并存,没有哪一种具有统一其他方言的影响力,路德站在和教会权威对立的民间立场上,在萨克森方言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各种方言和词汇,竭力使各地老百姓都能理解之。因而,明治政府企图用居住在政治首都东京、受过教育者所使用的语言为基础建立日本标准语,并不能完全效仿德国标准语的建立过程。上田万年虽然知道德国的情况,但他依然提出日本的标准语当以东京方言为基础[22],而森鸥外针对东京方言的语格进入言文一致体并被确立为一种新的文法规范所提出的异议,则很可能缘于他深刻地认识到了德国方言和标准语之间的关系。森鸥外留学德国时并未一直住在首都,而是分别在南部的慕尼黑、东部的德累斯顿以及北部的柏林三个地方居住和学习,他回国后发表的“留德三部曲”也是以这三个不同地区的故事为素材创作的作品。
《独逸日记》,是森鸥外在留学期间(明治17年10月至21年7月)写的日记。
表面看来,森鸥外的批评似乎可以被解读成他对作为政治首都的东京变成标准语的发源地提出的异议,或者可以说,正像柄谷行人指出的那样,这是森鸥外对日本近代化体制装置的抵制。《言文论》所反对的山田美妙一派的论述也加强了这种印象。山田美妙在《言文一致论概略》中强调,明治前的江户语就具有全国标准语的历史和地位:“当时是封建制度,各大名突出各地语言的差异”,但是,因为中央政府和参勤交代制度的存在,“唯独在江户才形成了语言的混合”,“各地人都多少接触过江户语的语法。所以江户语最终十分普及也是不可避免的”。[23] 山田美妙一直强调江户曾经是日本的政治中心,因而江户语具有构筑标准语的基础。山田美妙所说的是从明治前的江户到明治后的东京作为政治中心的历史地位,以及这一地位在标准语建构方面所具有的自明性优势;与此相对,1884年,东京文理科大学校长三宅米吉曾提出过“语言上的分权主义”,强调各地方言不存在孰优孰劣,反对强行制造以一地语言为基础的标准语(详见『江』:84)。也就是说,辩论的双方都想建立统一的国语,但分歧就在于是否应当以东京方言为基础语言。
1868年底,十六岁的明治天皇从京都前往东京
考虑到东京方言在明治时期的变化,我们会发现森鸥外对于标准语的态度其实更为复杂。他并非完全因为东京强势的政治力量才反对东京语作为标准语,而是认为东京语的语言基础相对薄弱。1868年,江户开城,此后,幕府的家臣和武家贵族纷纷逃离江户迁往静冈,城里剩下的多是下层武士和市民,以及以萨摩蕃为主的地方武士集团。到森鸥外写作《言文论》的明治二十年代,东京的人口从最初开城时的26万上涨到了约130万,其中以外来者居多,而江户本地人口的数量和阶级属性并没有显著变化,即主要由平民和下层武士组成。此时所谓的东京语并非“东京的语言”,或者说“住在东京的人说的语言”;江户方言,即后来所说的东京语,是保留了江户传统的下町方言[24],同时,由于江户本地人口在比例上的衰退,江户语,也即当时正宗的东京方言越发凸显其地方色彩。日本学者杉本孜认为,正是东京语浓烈的地方色彩以及使用人口数量不占优势,才构成了以东京受过教育者的语言为基础来重新构建标准语的契机[25]——这种具有浓烈江户地方色彩的方言正是日本标准语运动中要清除的元素。杉本孜也在《东京语的历史》一书中谈到了标准语的基础,认为江户语是一种表现人的活动结果的都市语言,其中包含了下层阶级使用的下町语词和文法,有别于代表日本长久政治中心的上方语[26]传统(详见『東』:195)。在杉本孜看来,明治以后,在所谓东京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标准语便是要实现从体现东京原有都市生活特色的东京语向体现日本政治特色的东京语的转换。杉本孜和森鸥外都并不赞同将东京语作为标准语,但杉本孜是站在江户原有下町社区的立场上,反对强势的政治权力剥夺了原有东京方言的市民底色的做法;而森鸥外反对将东京方言作为日本国文基础的原因却恰恰相反,他看到的正是东京方言的俗语底色不适合成为一国之语。
杉本孜也《东京语的历史》封面
其实,在德国,路德翻译《圣经》的语言也并非真正来自民间,而是以德意志中部和南部宫廷以及政府所使用的部分官方语言为基础,随后借助印刷技术将翻译推广于民间。[27]因而,森鸥外和上田万年都应当知道,即便是德国,与宗教用语拉丁语相对的“方言”也并非来自民间的俗语。森鸥外在《言文论》中之所以对语尾词“です”从东京方言进入日文书写系统不满,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些语尾词的世俗性。“だ”和“です”正是言文一致家们所尝试的用现代日语来创作近代文学的成果。例如二叶亭四迷《浮云》第一篇(1887)的语尾是“だ”;山田美妙的《武藏野》(1887)和《夏木立》(1888)语尾也都是用“だ”;山田美妙的《蝴蝶》(1889)采用了“です”调。最初的这批文学改革者都是出生于江户、后来留居东京的人。当然,从日本语言语法和翻译角度来研究语尾词“だ”和“です”历史的著作繁多,在此不予赘述,不过,杉本孜对江户世俗传统的研究也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地方历史视角。“です”本是古已有之的用法,但是在江户时代多为艺妓所用,和表示轻薄口吻的“でげす”意思相同,即便是一般的商人、工匠,或是稍有身份的人都不用这一说法。据说在明治之前,乡村武士来到江户,在柳桥、新桥一带听到艺妓使用“でげす”,以为这是江户的普遍用法,便加以模仿,随后这种用法就在江户流传开了(详见『東』:274)。而另一种语尾用法“であります”也有类似的历史。明治初期,使用语尾词“です”较多的是新一代从地方到东京的官吏和学生。明治10年左右,“です”出现在《读卖新闻》中,到明治21年,即森鸥外写作《言文论》的同一时期,“です”便作为“でごさいます”的缩略语被收录进英国的日本专家张伯伦(B.H.Chamberlain)所编撰的《日本口语文典》中(详见『東』:276)。所以可以看到,在明治以后现代日语的形成过程中,句尾词“です”一方面是从用训读方式引进新名词时产生的句尾形式中发展起来的,有着类似于“でごさいます”的意思;另一方面,它也裹挟着江户复杂的文化背景(详见『江』:76)。
结合《言文论》主要探讨的是文章的雅俗问题来看,森鸥外之所以反对将东京方言中的语格吸收到散文写作中,有可能正和“です”在东京方言里的“俗”历史有关。1910年,森鸥外在用言文一致体创作的小说《青年》中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从萨摩旧地来到东京的青年小泉纯一郎初到东京,因寻访知名作家大石路花而和他的女佣进行了对话。此时,他尝试的可是“平日在乡下读小说时学到的东京话”[28]。这位家境优渥、想以写作为生的萨摩青年“就像使用不习惯的外语那样,边想边说,一字一顿”[29] 地用东京语与女佣进行了来东京后的第一次对话。小说中这一虚构的场景不仅标志着言文一致体在国语改革中的最终胜利,同时也具有历史的象征意义,标志着明治维新后建立起来的新的日本世俗世界对于武士旧传统的胜利,而森鸥外想必对这两种胜利都不无惆怅。
1888年在普鲁士王国柏林市与日本学生在一起。
森鸥外出生于石见国津和野藩,十岁移居东京,他的父亲也在次年携全家搬到东京并开设了医院。可以说,森鸥外是抱着青云之志“上京”加入明治政府的。1872年在东京学习德语备考医学院时,森鸥外住在位于神田小川町的日本思想家西周的家中,上大学后移居本乡,两处居住地都在东京新型知识人圈所在的地铁山手线经过的区域内,与东京的下町区域没有交集。而倡导在东京人使用的语言基础上发展标准语的上田万年是藩士之子,出生在尾张藩(即名古屋)下屋敷,也就是远离江户城的郊外。虽然两人对标准语的主张不同——前者直接拒绝以东京方言作为语尾规范,后者则认为应提升东京语地位——但两人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所使用的都不是具有江户传统的下町市井语言,也就是说住在东京的受过教育者使用的语言其实正是森鸥外与上田万年他们自己的语言。[30] 如果森鸥外不用文语体而用言文一致体创作“留德三部曲”,很难想象他要如何用自己的方言或是东京方言直接转述分属于德意志不同地区、隶属于不同阶层、生活在不同时代的德国男女老少的方言,这用当时的日文是办不到的。毋宁说,森鸥外自己也从未想过要这样做吧。显然,与坚持使用一种以方言为基础的日语相比,森鸥外设想的是创造一种更具普遍性的国文。
森鸥外在柏林的住所
与此同时,倡导新语格的言文一致论者山田美妙虽然主张使用东京俗语,但他的理由无非也是“江户有中央政府”,而且今天的东京、未来的东京都将是日本的首府[31],这只是一种基于政治中心的诉求,而不是对于江户文化的强调。正如上文所言,柄谷行人将森鸥外放置在与言文一致体共同建立起来的日本国家体制框架之外。然而从方言的角度来看,森鸥外与山田美妙两人之间其实存在着一种奇妙的联系,虽然森鸥外反对以东京方言为中心的标准语,而山田美妙则提倡以东京方言为基础的言文一致体,但二者从根本上都是在否认东京的地方传统,同时认同新建立的明治政府中央体制,从这点上看,上田万年与他们也并无二致。他们之间这种隐含的相似性是被狭隘的言文一致视角所遮蔽的盲点,而这一盲点只有在日本国语与国文的创立历史中才得以显现。
3
理想的国文
《言文论》开篇即提出模仿死文“无助于国文发展的目标”(「言」:76),文章最后则以落合直文与山田美妙“两派同样都期待我国新国文的振兴”(「言」:84)一语结尾,可见虽然森鸥外讨论的是言文问题,但他在写作时考虑更多的是日本的国文问题。或者可以说,森鸥外正在用其理想的国文构想来丰富言文一致体。
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后,日本发起了以建设日本国民国家的语言和文学为目标的国文运动,《言文论》的写作正值此时。《言文论》发表的同年,博文馆开始刊行落合直文参与校订的《日本文学全书》,至1892年完成时,该系列收录了到中世为止的24册文学作品。[32] 四年后,博文馆的《帝国文库》又继续刊行近世文学。《言文论》刊出的前一年,以“本邦固有文学”为中心的《日本文学》创刊,1891年该刊更名为《国文学》。[33] 当然,不能忘记的是,“国文”兴起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帝国宪法及教育敕语的颁布。森鸥外在宪法颁布前一年回国,宪法颁布一年后创作了《舞姬》。后来任文部大臣的井上毅在参与宪法制定的过程中,提议将汉文“统治”一词用“纯粹日语”的“治らす”表示,显示出进一步去除汉字并同时向和文及日本历史回归的国家意图。[34] 森鸥外自然不会忽视明治政府的这些动向,在《舞姬》里通过“天方大臣”这一形象暗示了日本内阁交替与条约改正运动。[35]
井上毅任文部大臣后废弃汉文,明确倡导国文概念,而落合直文等少壮国学者也在此之后受到了礼遇[36],不久便开始了一系列国文和国语教科书及读本的编撰工作。1897年,落合直文开始编撰《中等国文读本》,收录了森鸥外的多篇译作。[37]国文运动兴起于井上毅提出向日本历史回归的语境之中,然而森鸥外和落合直文等在1890年前后提出的国文改良主张,并非简单回归日本和文的历史传统,也并非纯粹出于对国文的研究,而是要在明治以后的国语改革中,将国文研究“运用于实际”,是针对当时国语文体改革而提出的改良国文的主张。[38]经过早期废除和制约汉字的运动,到明治二十年代,和文的概念已经被国文以及在此基础上混合汉字与和文的文体所取代。
落合直文像
既然反对俗语的语格进入日文,那么森鸥外又是如何构想国文的呢?在《言文论》写作的同一时期,落合直文在《文章的误谬》(1889年)和《将来的国文》(1890年)中指出了当时国文的种种弊端:“我国的文学社会非常混杂,文体也各种各样。”[39]根据他的统计,当时所谓文体有汉文体、翻译体、小说文体、书简文体、言文一致体、歌谣词曲体等,不胜枚举。落合直文关心的是各类文体中混乱的日文文法,在他看来,文应当比言具有更严格的规则,因为所谓文章本是言语的连缀,若无文法规则,言语的错误往往会变成书写的错误。[40] 和森鸥外一样,落合直文也认为国文应当完全遵循语言的规则,但他并不同意言文一致论者直接以言为文的主张。在《文章的误谬》中,落合直文例举了19种文法错误[41],其中一类便是助辞的错误。他说,在日语中有各类助辞,“有表示普通的过去,有半过去,有自然的过去,有使然的过去,有惊叹的过去,也有确定的过去。各种意味不同,不应该混用。而今人不加区别,けり党就只用けり,ぬ派就只用ぬ,つ团就只用つ,たり帮就只用たり,き组就只用き”[42]。总之,他批评十种助辞只用其中一种、弃用其余数种的做法是一种经济主义行为。[43] 可见,就像森鸥外在《言文论》里提到的那样,落合直文并不反对以文写言,但他认为言文一致体应该具有更高的品位,而不应一味屈从言的规则,因为正是如此才会在语言中留下了较多的错误。小森阳一曾指出,山田美妙等人在日文单词五段活用的连用形后加上“て”“た”等连接词时,会出现促音变,这就将很多不规则的发音引入了书面语中,并使用言部分[44] 最大限度地发生了语法变化(详见《日》:163)。这种用法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将东京语中下品的使用法引入标准语外,还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典型的语音中心主义的做法,即用书面语摹写音变的同时不惜令用言部分发生语法变化,这正是落合直文和森鸥外所指出的语言中的错误。
落合直文所提到的助辞问题关系着日语表达中的时制问题。通过使用恰当的助辞和时间提示词,日语能表达多种时态和相的组合,但后来确立的现代日语主要沿用了现在、过去和将来三种时态,由つ,ぬ,たり,り等日语助辞表现时制的复杂性则脱落了。当时,山田美妙曾就助辞结尾词问题,对国文论者提出过针锋相对的意见。他在《言文一致论概略》中说,俗语动词的时态是反对论者集中攻击的焦点,他们都认为俗语的时态是不完整的;但其实俗语中的时态并不像国文论者所说的那样混乱而无序,因为俗语只有四种正确的时态,而且只要四种就足够了,即现在进行时、过去时、将来时和现在完成时;而原来的古文,则如“已经灭绝的乳齿象不会再次复苏”。[45]
森鸥外《青年》封面
山田美妙所提到的俗语时态“只要四种就足够了”无疑是对文的最低要求,也是落合直文所说的“经济主义行为”,这或许正是言文一致体的局限。森鸥外后来在小说《青年》中这样讽刺当时所谓的作家:“被人追捧的主人公、著名作家大石路花既不说要练习的话,也不说要修行的话,只说写出来是最重要的事情,所谓文章就是这么一回事了。如果要写拟古文的话,是需要不断练习的,大石本身也不会,他所写的东西里就有很多假名的错误,不过他说不用管这些,接着写下去就是了。”[46] 这在森鸥外看来或许也是言文一致运动的必然后果。
森鸥外的《言文论》在文法层面主要针对的也是句尾的时制问题。他在同一时期另一篇非常短小的《言和文》中再度详细讨论了《言文论》的主张:
国文的时制比当今言的时制要好。当言转换成文的时候,应当改变言的时制,这个言也就能非常确切。当今的言文一致家真的想要使文成为文的话,仅仅在句尾增加俗语是完全不能做到的。[另一方面,]若有人真的厌恶将句末助辞变成俗语的时制而大量使用名词结尾的话,也不能说是遵从了国文的句末助辞规则。[47]
作为自己主张的实践,森鸥外在《舞姬》中使用了大量的语尾助辞。在此之前,森鸥外在留学途中曾用汉文体写过《航西日记》,到西贡时,还曾赋诗一首。但是,正如当今的评论家所言,由于使用了汉文体,《航西日记》基本上是一种脱时间的静态文体。[48] 只有使用了文语体,即充分调动落合直文所提到的日语助辞的时制功能后,《舞姬》才得以包含手记写作的现在时间和手记记叙的过去时间这样一种双重时间结构。柏林这座城市是随着主人公太田丰太郎过去的意识,借助视觉描写展现出来的。丰太郎与爱丽丝会面时,提示词“现在”将过去的时态转换到了现在的时态;等丰太郎去爱丽丝的房间时,时态又转变成了进行时。时态的转换不仅提示了丰太郎的意识和心理变化,也提示了场景和地点的转换。可以说,全文正是通过不同的时态将不同的场景缀连起来的。[49]
但是要说森鸥外的《舞姬》和《言文论》是言文一致尝试的一种倒退是不公平的。因为正如柄谷行人和小森阳一都已经指出的那样,《舞姬》除了句尾不使用“だ”和“です”外,其他做法都更接近西洋的文体,具有更强的写实性,能够轻而易举地被翻译成西语。森鸥外的文章被作家谷崎润一郎称为平明派的文章,即“每一个细节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没有一点暧昧模糊之处,文字使用正确,语法也没有错误”[50]。在如何使文成为文的问题上,森鸥外或许比同时期的言文一致家走得更远。
4
翻译中降生的传统
那么,森鸥外使用日文旧语格的理想国文构想来自何方呢?《言文论》里所提到的落合直文、小中村清矩等这一代的日本国文学者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他们都不排斥“洋学”,甚至主张要在研究日本国体和国文时考虑吸收西洋知识。森鸥外之所以在如何使文成为文这一点上得出和言文一致家不同的结论,原因就在于他能够在跨文化的场域中思考日本的国文问题。森鸥外显然是支持落合直文所提出的旧语格的,而且也在同一时期运用旧语格创作了《舞姬》。但是,森鸥外并非复古主义者,他提出要使用今言,用今文写今言,不写复古的文。《舞姬》展现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最初的留洋经验以及与异国女性交往后惊心动魄的内心世界;与此同时,小说也用假名和汉字所组成的词汇大量展现了柏林的风物人情。《舞姬》的情节究竟是以中国白话小说中常见的才子佳人始乱终弃的故事为原型,还是以《源氏物语》等国文学中的“恨”(恨み)为核心,仍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但从题材上来看,《舞姬》无疑是个跨文化文本。这一跨文化视角同样可以重新审视有关“和汉洋三文脉的调和体”[51]或“和汉洋折中的新文体”[52] 的论说。
安万侣曾在为《古事记》所作的序中写道:“上古之时,言意并朴,敷文构句,于字即难,已因述者,词不逮心,全以音连者,事趣更长。是以今或一句之中,交用音训,或一事之内,全以训录。”[53] 这段话被日本语言学家柳父章称为日语感觉的原型。它一方面是对词不逮心的自觉,即自觉到汉文词汇不足以表达日本人的情感;另一方面也指出“全以音连者,事趣更长”,即意识到和文在文体上拖拉繁复的缺陷。因而,安万侣的做法是在一个句子的某些部分将摹写“口语”的日语表达与作为“词”的汉字混用,而另一些部分则只用汉字表现。在柳父章看来,这便是日本书面语的原型。[54] 明治时期以文章通俗而著称的福泽谕吉曾谈到过单靠俗语难以成文。他在《福泽全集》的序言里写道:“俗文不足之处用汉文字来补足,非常方便,因而汉文绝不可弃。”[55] 坪内逍遥也在《小说神髓》的文体论中指出过明治时期文体的难题。他说,雅文体“优柔闲雅”,“自有古雅的情致”,但“缺乏活泼豪宕之气”,“袅袅缺乏气力”,无法描写豪放的举动和跌宕的情景[56];而取自口语的俗文体则易懂而活泼明快,但是可能会“失之音调的乖离,或气韵的野鄙,因此极为风雅的想法写起来就变得十分粗野”(『小』:7)。同时,俗语有冗长之弊,且无语法规范,缺乏音韵之美,尤其不适合叙述和描写(详见『小』:9)。从安万侣到坪内逍遥,他们都意识到可能要在跨文化的体系中才能找到创制优良日文的方法。
坪内逍遥像
明治时期通行的书面语主要有两种情况,即含有较多汉字、平民难以理解的汉文训读体以及整体平易、平民容易理解的汉文训读体。[57] 但不管哪种情况,汉文训读调已经构成了书面语的底色。虽然《舞姬》被认为是雅文体的实验作品,但仍然留有强烈的汉文训读底色。例如,小说中“肠一日九转”(腸日ごとに九廻す)之类表述主人公感情的文字其实是对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是以肠一日而九转”的翻译。[58] 日本文学中受到汉籍影响的情况不胜枚举。[59] 更为重要的是,在杉本完治看来,《舞姬》文体上的特点,即主语+述语的表达方式正是受到汉文的影响,以述语为中心的文体使得《舞姬》的句子有别于一般文语体的冗长而表现出短小精悍的特点。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汉文体底色的存在,《舞姬》才表现为文学史上通常所说的“和汉混淆”的文体。[60] 有意思的是,在杉本完治看来完全属于汉文句型的底色,在矶贝英夫看来则类似欧语文脉中的句法逻辑,由此《舞姬》才得以区别于一般流于情感描述的和文学,它除了具有准确描写现实的能力外还带有很强的说理性。[61] 姑且不论是汉文特色还是西文影响,《舞姬》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跨文化的混杂文体,它也由此成为近代日文书写系统的典范。
原本训读体就是一种翻译手段,是日本文人在接触中国文献时,通过助辞“てにをは”对汉籍所做的“日本化”处理。[62] 正如福泽谕吉所说的那样,明治以后,这种“日本化”的翻译手段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日本人由吸收中国文化转向对西洋学术思想的接受,但不变的是他们仍需借助汉字和汉文词汇来书写和阅读。[63] 问题是,如森鸥外所说,“若有人真的厌恶将句末助辞变成俗语的时制而大量使用名词结尾的话,也不能说是遵从了国文的句末助辞规则”。也就是说,要创制真正的国文,在文化翻译的过程中,应该如何写用言部分是日本文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日文的特点是动词后置,句尾具有词形变化的用言部分表示时态和感情,与叙事的逻辑真正相关;而多以汉文名词表述的体言部分不参与时态和感情的表达,无法建立起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据柳父章的研究,日语口语本不是逻辑清晰的文体,说话者并不完全结束句子,而是积极与对话方保持交流,因而说话者说出的是一个个不完结、不独立的句子。[64] 言文一致家二叶亭四迷选择口语体后,直接面对的就是叙事逻辑不清的问题,所以他才会在写作的同时需要直译屠格涅夫的作品以求调整自身的语感。他在翻译外语的过程中习得了通过使动词词尾变成“た”来结尾并厘清句子间关系的做法,由此形成了新的断句意识。[65]
福泽谕吉像
森鸥外自然也为如何拥有更优秀的叙事与抒情方法所苦恼。一方面,他在一系列讨论日文朗读的文章中提议应该按照日文的文法规则来断句,并注意文章的结构、组织、分段和助辞的用法等方面[66];另一方面,他也依靠翻译来提升写文的品位,这不仅包括上文所提到的汉文训读调,还包括对西洋文体的借鉴。在发表于1891年的《德意志文学的隆运》一文中,森鸥外表示自己喜欢用直译西方作品的方法向日本输入西洋的句法。他认为这样做并非盲目崇拜西洋的句法,而是希望承认西洋句法的有趣之处及其优点,进而改善日文句法。[67] 也就是说,森鸥外在国文和洋文之间也建立了一种翻译和对应关系,这为理解上一节所提到的他启用旧语格写作提供了新的视角。作为理想国文一部分的旧语格自然是为了表达更为清晰的逻辑关系,然而,森鸥外使用旧语格的做法并非简单的复古,而是一种对“传统的再发明”,即在翻译过程中重新发现日文助辞在表意上的现代功用。
明治以后,“国文”的参照系除了自古以来的汉文外,还有荷兰语、德语和英语等西洋语言。森鸥外在《言文论》中提到,日文中存在“语脉混乱不堪”的问题,是因为“我国没有辞典,因此这是很容易发生的。如果有辞典的话便不会有这样支离破碎的文了吧”(详见「言」:79)。事实上,1886至1898年正是日本国文文法辞典体系的确立时期。就在森鸥外呼吁编写辞典的那一年,落合直文和小中村义象合编了《日本文典》,落合直文还单独出版了《普通文典》。[68] 然而,直到1876年为止,日本国文典仍然遵循西洋文典的处理方法,将时制主要编排在动词的类目中。1877年之后,表示过去、现在、未来的词才开始出现在助动词分类中,时制的表述从动词的活用等开始扩展到助动词的分类,这种倾向在明治后期愈加明显。[69] 有人或许认为在语尾使用旧语格是一种对和文传统的接续,然而事实却正与此相反,在明治二十年代的文坛,落合直文和森鸥外再次将旧语格抬升为一种文体规范,其实是为了重新激活明治二十年代以后在和汉洋三重文化场域中的国文传统。
明治末年的皇典讲究所
森鸥外写作《言文论》时,“国文”尚未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和学科被确立,它的建立本身就是一种对传统的再发明。而森鸥外和落合直文便处于这个国文创制的历史节点上。落合直文的《文章的误谬》发表于1889年皇典讲究所的期刊《皇典讲究所讲演》上。皇典讲究所成立于1882年,1889年进行了改革,根据其“改正趣意”来看,改革后的皇典讲究所主要是一个以推进国学研究为目的、致力于日本文献研究、设立国学院、刊行国学相关著作的国学研究与教育机构。[70] 当时所谓的“国学”超越了神道、律令、国史、歌学、有职等领域,纳入了国文学、国语、国文、法制和经济等各个科目。从《皇典讲究所讲演》1889年的目录来看,该刊发表的文章既有有贺长雄的政体和历史断代研究,也有落合直文的叔叔落合直澄的国语研究。此后,皇典讲究所内设立了国学院,在强调通过专门研究“国史、国文、国法”以便成为“我国民国家观念的源泉”的同时,该机构也并未限制国学院文献研究的边界,而是认为应当补充中国和泰西的道义之说。[71] 皇典讲究所成立的同时,东京帝国大学也设置了古典讲习科,校长加藤弘之聘请了《言文论》中所提到的小中村清矩担任教授,久米干文担任讲师。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这个古典讲习科并非只有国文,也设置了汉文科。[72] 可见,由于并不排斥广义的文化翻译,1880年代的“国文”或“古典”的概念远比坚守十八世纪声音主义的国学家们所定义的“国语”概念要宽泛。
落合直文当初所致力于改良的优雅国文被称为“新国文”,他设立了超越拟古文及旧古文陈腐形式的清晰目标,可以说是一种现代的追求。关于这一点,日本国文学者、落合直文早期弟子金子薰园的观点更能清楚地概括:“新国文”的骨架是汉文,衣服是国文,而且不使用罕见生僻的古文,也并非传统拟古文那样柔弱的文章,落合直文在汉文的骨架上只吸收国文脉中在他看来有价值的部分。[73] 可见,与复古倒退的定说相反,《言文论》及作为其背景的新国文运动力图用日本历史中一以贯之的翻译手段创制出明治时期日本国文的新形式。森鸥外和落合直文希望用这一新国文的概念修正言文一致体用言部分的鄙俗,为尚未定型的言文一致体带来新的活力。
昭和女子大学图书馆为明治18年松月堂刊行的
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中将言文问题看作日本独有的问题(详见『小』:3),但森鸥外却在《言文论》开篇就说“言必在文之前发展,而文则在其后直追,这一点参照世界各国的史籍便可知”(「言」:76)。日本的言和文的问题不是日本特有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问题。在森鸥外看来,简单地将东京方言提升为标准语,甚至墨守旧有日文国文传统,都不可能解决这一普遍的问题,必须要像《舞姬》的故事所象征的那样,经由不同文化的交锋来建立一种新的、混杂的,因而也是普遍的日文文体。
结 语
从森鸥外的《言文论》及其同时期的一系列论述和文学创作中可以看到,对于森鸥外而言,近代以后的言文关系从来就不是简单地去除汉字或像言文一致家们所倡导的那样直接用口语写作这么简单,作家们面对的问题也不仅仅局限于言和文的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民族国家诞生后,甚至在帝国扩张时,如何创制出一套新的、“普遍”的文的系统,以及让经历了最初言文一致革新后的文成为文。这其中自然包括言文一致家们所呼吁的减少使用汉字,而多使用俗语;但另一方面,森鸥外也看到光靠这些主张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厘清句子的逻辑关系,而这势必意味着文法结构的重新发明和创制。在这样的考虑中,森鸥外提出不应当引入东京方言的句尾形式,而应该启用日文旧语格,并践行一贯的翻译原则。森鸥外的这些主张既是对国文的设想,也是针对当时言文一致体的发言。像柄谷行人那样认为森鸥外并未将各种古文的时态统一到语尾词“た”上,且与言文一致家们所使用的“た”相对立的这种说法,事实上夸大了森鸥外与言文一致家们的差异,且忽视了他们双方都葆有着在现代国家体制建立过程中创制国文的自觉。此外,借助对近代德语及德国文学的理解,森鸥外重新审视了国文传统。正如加藤周一曾提到的那样,“不消说鸥外并非一个单纯的保守主义者”,“只要是关于学问的事,他就是一个彻底的西方化论者”。[74] 由此可见,森鸥外对言文的构想、对旧语格的呼吁也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复古,而是翻译的产物,是对传统的再发现,因为“在明治二十年代唯有翻译工才是新文体的创造者”(《日》:154)。
注 释
[1]路功处士是明治作家内田鲁彦的笔名。
[2]详见磯貝英夫『文学論と文体論』,東京:明治書院,1980年,第173-174頁。
[3]文语体是在平安时代(794—1185)贵族口语基础上形成的日文,多用于公文等正式的场合,明治时期指与日常口语所用的文体相对的文体,与吸收口语语法和词汇的言文一致体相对。雅文体指平安时代用假名写成的文体,与文语体接近,但所针对的是用汉字写成的汉文。由于两者所指接近,对于森鸥外明治二十年代的文体,评论者根据他们所针对的具体问题到底是俗语还是汉文,有时使用雅文体,有时使用文语体称呼之,本文对所引文献中所使用的概念不作变更。
[4]小森阳一《日本近代国语批判》,陈多友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2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日》”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5]元禄文学指日本元禄年间(1688—1704)主要在京都一带发展起来的“町人”文学,主要代表作家有井原西鹤、近松门左卫门、松尾芭蕉。明治二十年代,尾崎红叶等作家借鉴了当时元禄文学的手法,写作了《金色夜叉》等被称为复兴元禄文学的作品(详见陈多友《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3页)。
[6]详见成春有《日语汉字音读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8-41页。当然,进入二十世纪后,言文一致运动便进入了鼎盛期,1922年以后,日本的报纸全面实现了口语体。
[7]详见浜本純逸『「国語及漢文」(いわゆる「国語科」)の成立:中等学校国語教育史(四)』,载『国語教育思想研究』2015年第10号,第6頁。国语即日语(Japanese language),指宽泛意义上的近代日本民族国家的语言,包括国文、汉文训读体等当时出现在书面中的各类文体。经过初期的文体改革后,当时逐渐稳定下来的国语是包含汉字的体言部分及使用和语的用言部分的混合文体(漢字交り文)。
[8]详见山口謠司『日本語を作った男 上田万年とその時代』,東京:集英社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2016年,第12頁。
[9]森鴎外「言文論」,收入森鴎外『鴎外全集』(第二卷),東京:鴎外全集刊行会,1924年,第76頁。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言」”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0] 森鴎外「朗讀問題」,收入森鴎外『鴎外全集』(第二卷),第193页。
[11]指《百花园》《花筐》等依据发音将落语表演摹写下来的笔记。
[12] 因为《日本书纪》《古事记》均包含用日本读音来标记汉字的做法,故保留了古代日本的口语发音。
[13]详见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95页。
[14]详见山本正秀『言文一致の歴史論考 続篇』,東京:桜楓社,1981年。
[15]详见山本正秀『近代文体発生の史的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65年,第586頁。
[16]详见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64页。
[17]详见柄谷行人《岩波定本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40页。
[18]详见小倉斉「森鴎外初期の文体意識に関する覚書」,载『愛知淑徳短期大学研究紀要』1988年3月第27号,第24頁。
[19]详见上田萬年「國語と國家と」,收入上田萬年『国语のため』,東京:富山房,1897年。
[20]详见水原明人『江戸語·東京語·標準語』,東京:講談社,1994年,第83頁。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江』”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21]详见上田萬年「標準語に就きて」,收入上田萬年『国語のため』,第54頁。
[22]在小森阳一看来,所谓“标准语”应当是有望在未来通过调查发现的、并将它改造后才可称为“标准语”的日语,但上田万年等人却以透支未来为代价,将未来的概念认定为业已存在的事实(详见《日》:150)。
[23]详见山田美妙「言文一致論概略」,收入山田美妙『山田美妙集』(第9巻),京都:臨川書店,2014年,第5頁。
[24]江户东部商人、手工业者等居住的区域被称为下町区。
[25]详见杉本つとむ『東京語の歴史』,東京:中央公論社,1988年,第257-261頁。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東』”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26]上方语指的是京都、大阪使用的日语。
[27]详见上田萬年「標準語に就きて」,第54頁。
[28]森林太郎『青年』,東京:籾山書店,1913年,第4頁。
[29]森林太郎『青年』,第4頁。
[30]上田万年和山田美妙等人主张之间的关系需另著文讨论。
[31]详见山田美妙「言文一致論概略」,第5頁。
[32]详见金子薫園「落合直文の国文詩歌における新運動」,收入十川信介編『明治文学回想集』(上),東京:岩波書店,1998年,第304頁。
[33]详见平田由美「反動と流行―明治の西鶴発見―」,载『人文学報』1990年第67期,第187頁。
[34]详见夜久正雄「大日本帝国憲法と井上毅の国典研究」,载「亜細亜大学教養部紀要」1981年第23号,第77頁。
[35]自1870年开始,明治政府致力于废除1850年代幕府时期与西方国家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直到1894年7月与英国签订了新的日英通商条约后,日本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才得以逐一废除。1889年12月成为首相的山县有朋曾于1888年12月至1889年10月访欧,其随行军医为森鸥外在东京帝国大学就读时的同学贺古鹤所。由于贺古的引荐,山县有朋日后成为森鸥外仕途上的庇护(详见陈多友《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第52页)。
[36]详见窪田空穂「明治前期の国語国文界の見取図」,收入十川信介編『明治文学回想集』(上),第319頁。
[37]森鸥外所作篇目的收录情况可参见《中等国语读本编纂趣味书》(落合直文編『中等国語読本編纂趣意書』,東京:明治書院,1901年)所附十册目录。不过,从1903年(明治36年)起,《中等国文读本》进行修订时更名为《中等国语读本》,这正是在山本正秀所谓的从明治33到明治42年的言文一致确立期内。据日本学者菊野雅之的研究,这一时期《中等国语读本》中所收录的言文一致体的篇目越来越多,呈现出“国语”逐渐替代“国文”的趋势。不过,这已经是后话(详见菊野雅之「落合直文『中等国語読本』の編集経緯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二冊の編纂趣意書と補修者森鴎外·萩野由之」,载「語学文学」2015年12月第54号,第35頁)。1903年落合直文逝世后,帮助修订《中等国语读本》的正是森鸥外《言文论》中提到的另一位国学者萩野由之。
[38]例如与森鸥外和落合直文在同一时期共同参与国文研究的小中村清矩就提出国学研究既要解决实际问题,又要吸收西洋学问(详见小中村清矩『陽春廬雑考』[巻八],東京:東京築地活版製造所,1898年,第9頁)。
[39]落合直文「文章の誤謬」,收入落合秀男編『落合直文著作集』(第1巻),東京:明治書院,1991年,第313頁。
[40]详见落合直文「将来の国文」,收入落合秀男編『落合直文著作集』(第1巻),第359頁。
[41]详见落合直文「文章の誤謬」,第317-326頁。
[42]落合直文「将来の国文」,第357頁。
[43]详见落合直文「将来の国文」,第358頁。
[44]名词、代名词、数词等没有词尾变化的独立词为体言;动词、形容词、形容动词总称为用言,有词尾活用变化。
[45]详见山田美妙「言文一致論概略」,第10-11頁。
[46]森林太郎『青年』,第33頁。
[47]森鴎外「言と文と」,收入森鴎外『鴎外全集』(第2巻),第92頁。
[48]详见森鴎外「日记·航西日記」,收入加藤周一、前田爱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6文体』,東京:岩波書店,1991年,第382頁。
[49]详见森鴎外「森鴎外·舞姬」,收入加藤周一、前田爱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6文体』,第441頁。
[50]谷崎润一郎《文章写法》,李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76页。
[51]山本正秀『近代文体発生の史的研究』,第580頁。
[52]山本正秀『近代文体発生の史的研究』,第586頁。
[53]安万侣《古事记》,周作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7页。
[54]详见柳父章『日本語をどう書くか』,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2003年,第183頁。
[55]福沢諭吉「福沢全集緒言」,收入加藤周一、前田爱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6文体』,第48頁。
[56]详见坪内雄蔵『小説神髄』(下巻),東京:松月堂,1887年,第3-4頁。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小』”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57]详见岡本勲「言文一致体と明治普通文体」,收入森岡健二編『講座日本語学』(7),東京:明治書院,1984年,第60頁。汉文训读指的是依日语文法解读汉语文言文的方法,实际也是一种翻译。
[58]详见杉本完治『森鴎外「舞姫」の全貌:言語学的研究に基づく考察』,東京:右文書院,2020年,第208頁。
[59]详见杉本完治『森鴎外「舞姫」の全貌:言語学的研究に基づく考察』,第334頁。
[60]详见杉本完治『森鴎外「舞姫」の全貌:言語学的研究に基づく考察』,第384-386頁。
[61]详见磯貝英夫『文学論と文体論』,第186-187頁。
[62]详见柳父章『日本語をどう書くか』,第13頁。
[63]详见柳父章『日本語をどう書くか』,第42頁。
[64]详见柳父章『近代日本語の思想―翻訳文体成立事情』,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2004年,第91頁。
[65]详见柳父章『近代日本語の思想―翻訳文体成立事情』,第85頁。
[66]详见森鴎外「逍遙子の朗讀説」,收入森鴎外『鴎外全集』(第2巻),第190頁。
[67]详见森鴎外「独逸文学の隆運」,收入森鴎外『鴎外全集』(第38巻),東京:岩波書店,1975年,第454頁。鲁迅的直译观与此类似,其所受影响是否来自森鸥外尚待考察。
[68]详见山東功「大槻以後:学校国文法成立史研究」,载『言語文化学研究』2012年第7号,第7頁。
[69]详见服部隆「明治期の日本語研究における時制記述」,载『上智大学国文学科紀要』2006年第23号,第30頁。
[70]详见松野勇雄『皇典講究所改正要領』,東京:皇典講究所,1889年。
[71]详见「國學院設立趣意書」,收入国学院大学編『国学院大学一覧』,東京:国学院大学,1930年,第6頁。
[72]详见窪田空穂「明治前期の国語国文界の見取図」,第317頁。
[73]详见金子薫園「落合直文の国文詩歌における新運動」,第305頁。
[74]详见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叶渭渠、唐月梅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第314页。
「 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