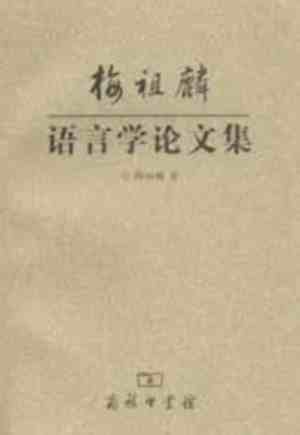闽南话是古汉语的活化石
《重新认识台湾话》序
文 | 吕正惠
一
我的好朋友郑鸿生,从小生长于台南府城的中产之家。他们家有文化,祖父一代上过私塾,能用闽南语读书音诵读中国古籍和唐诗宋词。父亲一代受过比较好的日本公学校教育,完全不会闽南话读书音,日语学得不错。鸿生说,父亲长大后,没有办法跟祖父沟通,因为祖父没有从日语学会西方现代化知识。鸿生是台湾光复后最早期接受国民党完整教育的年轻一代(他生于1951年)。他的国语学得不错,他能用国语流畅的表达国民党教给他的“反共”意识和现代化思想。现在情况反过来,没有学会国语的父亲,已经无法跟鸿生沟通了。鸿生三代之间彼此很难顺畅交谈,主要是因为他们家经受了两次政权转换,父亲没办法再学闽南语读书音,而鸿生则可以不学日语,直接学国语。虽然他们三代都讲闽南话,但在日常生活之外,祖父学的是闽南语读书音,父亲学的是日语,鸿生学国语,他们的知识语言是彼此不同的。鸿生高中以后才逐渐认识到这种困局,因此下定决心自己独立学习闽南语读书音(鸿生称之为“典雅闽南话”),从而学到了日常生活之外的另一套“台湾话”。这个时候,鸿生才完全清楚,他从小所熟悉的闽南话,其实主要是闽南话的“白话音”(即口语),他祖父所传承的那一套传统的闽南话读书音,因为殖民统治的关系,已经被日本人有意的切断了。台湾光复以后,台湾的闽南子弟基本上已经完全忘记了闽南语读书音那一套语言,他们现在学习的是中国大陆的国语(即大陆所谓普通话)。
文白异读示例
鸿生后来参加了傅万寿先生所开设的“典雅闽南话”读书班,系统的学习了闽南话的读书音,他可以用这一套读书音来诵读唐诗宋词和中国文化经典。但鸿生并不以此为满足,以他从小热爱中国文史的习性,他进而想追问一个历史问题:为什么闽南话会有一套读书音系统,还有另一套口语系统?透过阅读历史书籍,鸿生当然知道,住在中国北方的汉族因为中原战乱而辗转南迁。其中迁移到福建的最后形成了汉语方言中的闽语,而闽南话就是闽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鸿生花了很多时间阅读中国的历史和汉语语言学的历史,才逐渐了解北方汉族南迁到福建的过程;并且也终于认识到,主要在福建形成的闽南话(除了福建南部,浙江南部一小块地方,广东潮汕地区和雷州半岛,还有海南岛,都是闽南语流行区),为什么会产生口语和读书音两个系统。鸿生原来就读于台大哲学系,毕业后到美国留学,改学计算机,获得硕士学位。在计算机专业上工作了十多年后,终于下定决心辞职,从事自己一直深感兴趣的文史写作。他并不是一个专业的汉语方言学家,因此他谦称自己写的这本书只是“读书笔记”。
傅万寿,1939年生,从事汉文教学、诗词吟唱、古文朗诵已逾30年,毕生以追溯自源语文系统源流、探究河洛文化为职志,擅长诗词吟唱方式教学,被称为河洛话吟诵国宝级大师。
其实鸿生追寻闽南话形成过程的苦心,在讲闽南话的台湾知识分子中,是极少有的例外。台湾光复后成长起来的、讲闽南话的知识分子,都碰到一个类似的大问题,长期困扰着我们(讲客家话的也有类似的遭遇,不过这里只限于讨论讲闽南话的人)。最后他们(也就是我们讲闽南话的大部分人)把这个问题完全归罪于国民党。他们说,国民党和荷兰人、郑成功、清朝,还有日本人一样,都是外来的殖民者(先假装公正,把日本人也列入殖民者中),国民党把他们的殖民语言(中国话),也就是我们习称的国语,强迫灌输给我们,让我们不再能讲日语,只能改学中国话(曝露狐狸尾巴,明显偏爱日语)。而且国民党还非常瞧不起台湾话(即闽南话),禁止我们讲方言,所以我们才会台湾话也讲不好,中国话(即国语)也讲不好,我们这种语言困难,完全是国民党的“再殖民政策”造成的(其实正如前面所说,闽南话的读书音是被日本人有意切断的,主犯是日本的殖民政策,根本不是国民党。国民党教我们国语,起码是从外国话的日语回归到中国的通用语——国语)。
闽语分布图(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二版)
这是一种非常简化、非常荒唐、毫无历史知识的“胡说八道”。首先,“国语”只是汉语中的一种“通用语”,在国语之外,汉语还有很多方言,如吴语(上海话、苏州话等)、粤语(广东话)、客语、闽语(福州话、闽南话等)。国语和闽南话都是汉语,是汉语的分支,而日语完全是外国话,和中国话完全不一样(只是自唐代以后,日语不断的从中国输入各种词汇,所以日语中才有许多汉字)。另外,他们也不知道,闽南话除了日常口语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读书音,可以阅读中国经典和唐诗宋词,而这种读书音的失传,其根源就在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不过,由于长期以来台湾的闽南人对国民党政权的厌恶(国民党治台初期的许多劣政,也是不容否认的),以上这种“胡说八道”竟然深入人心,极难祛除。“台独”理论完全不知道闽南语和汉语的渊源关系,却把“国语”看成是中国话,而把“台湾话”看成是和中国话毫无关系的另一种话,把两者对立起来,好像是完全不相同的两种语言,这不是毫无历史知识的“胡说”吗?
吕正惠《战后台湾文学经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鸿生是深通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他根本不相信这种胡说。反过来说,正因为他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素养,他才会花大力气的写这样一本“读书笔记”。他想正本清源的告诉大家,闽南话是汉语方言中历史积淀最深的一种,从闽南话最能够看出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我完全能够理解鸿生的苦心,因为我也是从小讲闽南话的人,进了小学才开始学国语,也开始热爱中国文史。作为从小讲闽南话的人,我学国语的经验和鸿生极为类似。虽然我们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差距颇大,但我们在追寻闽南话和中华文明的历史关系时,却完全是心志相通的。
我比鸿生大三岁,因为生于年尾,八岁才入学,学制上比鸿生高两届。跟鸿生相比,我是纯粹的农民子弟,我生长的小村子在嘉义靠海边的地方,所以我跟鸿生一样,是属于嘉南平原上讲同一种闽南话的人。但我们村子基本上没有文化,在我的印象中,很少人会讲日语,日本的统治对我们影响非常小。这一点跟成长于府城中心的鸿生有很大的差别。因为父亲好赌,很早就卖掉农地,我从小学时代就迁居台北。所以我比鸿生更早认识到闽南话漳州音和泉州音的区别,如我们把“筷子”叫做tī,把“猪”叫ti,而我们所租房子附近的人,把筷子叫tū,把猪叫tu,我们偏漳州音,他们偏泉州音。还有一个经验对我来讲也很深刻,我的作文一直写不好,因为我的国语不如台北人好。一直到高中时代,我的作文才勉强跟上台北人。(鸿生讲得很对,根本在于城乡差距,而不是省籍差距。)
厦漳泉方言发音的差异举例(图片来源:徐荣《汉语方言深度接触研究》,2012年)
不过因为我很早就上台北,所以我中学时代就开始喜欢学习国文、历史、地理等科目中的中国文史知识(如果我继续待乡下,学习的机会就会差很多)。虽然我的数学、理化也学得不错,但在高中考大学时,我还是选择文组。我高中读的是建国中学,而建国中学很少人读文组,我们那一届全部1200多名考生,就只有22人报考文组,那时候我真够“勇敢”的吧。那时李敖正风行于台北读书界,我受李敖影响,已经决心要当一个中国文史学者。(鸿生联考时,受费孝通影响,由台南一中考上台大社会系,后来才发现,这种社会学跟费孝通的社会学毫无关系,才因仰慕殷海光而转到台大哲学系,那时候我已是本科四年级的学生了。)
图为《增补汇音妙悟》(1831),初版《汇音妙悟》为清朝嘉庆5年(1800年)晋江人黄谦(字思逊,号柏山主人,南安水头文半村人),据《闽音必辨》一书所编写的一部以泉州音南安腔为主的闽南语音韵学书籍。在台湾使用类似腔调的地区为汐止、三峡、林口等地。
我所以选择读文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高中时喜欢上了中国古典诗词,我在台大中文系读了七年书(从本科到研究所),一直以唐诗宋词为主要研读对象,我的硕士、博士论文写的也都是唐诗。正因为研究唐诗,我才开始注意闽南话。
我读本科三、四年级时,台大正流行英美新批评,我也很受影响。不过,我跟其他学诗词的不一样,除了新批评所重视的意象和结构分析之外,我还受到系里的资深教授郑骞先生的影响,也重视诗词中的格律。因此,我很容易就发现,诗词中的入声字和入声韵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很难深入理解诗词艺术的许多微妙之处。譬如,宋代词人柳永的《雨霖铃》整首押入声韵,而现在的国语是没有入声的,所以如果只用国语来朗读,就很难体会这首描写离别的词所表现的那种哽噎之情。我们班上有一位香港侨生,曾经在大家聚会的场合,用广东话朗读《雨霖铃》,让我深感意外,因为那种效果完全不是普通话所能比拟的。我知道闽南话也保留了入声调,因此努力的学习闽南话读书音,想要用闽南话读书音来朗读《雨霖铃》。刚开始念起来还不太顺,后来不断的练习,终于可以读得很顺。以后自己上课讲这首词时,就曾用闽南话读给学生听,让学生了解什么叫入声韵的特殊效果。
吕正惠《诗圣杜甫》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跟这一点有关连的是,因为普通话已经没有入声调,入声字在国语中分入平声、上声、去声三个声调,这样就变成不押韵了。很多唐诗宋词,现在念起来好像是不押韵的,最明显的例子,除了柳永的《雨霖铃》之外,还有李清照的《声声慢》(鸿生还举了李白著名的《将近酒》为例,证明在现在的普通话里,很多原来押韵的地方变成不押韵了)。五四以后写新诗的人认为写诗可以不押韵,可能是因为他们读古诗词时,在很多作品中并没有感觉到整首作品是有押韵的,这真是很严重的错觉。
《将进酒》闽南语注音(文读)
因为这层关系,又因为我自己从小在乡下一直讲闽南话,所以在大三碰到《汉语音韵学》(传统叫作《声韵学》)这门课,我就学得特别用心。考研究所时,《声韵学》是必考科目,单单这一门,我比这门科目的第二名足足多出三十分,这就保证了我一定录取。鸿生让我看他的书稿,以为中文系毕业生声韵学一定很内行,其实远远不是。中文系学生绝大部分都以学声韵学为苦差事,但求过关,一拿到学分早就忘光了(这里讲的是台湾的中文系,大陆的中文系就更不重视声韵学了,大陆凡研究古代诗词的,普遍不重视韵律,其偏颇更甚于台湾)。鸿生不知道,中文系学者能够读懂他的书的人,其实人数是相当有限的。因此,我很佩服鸿生,居然透过自我学习,懂得那么多汉语音韵学(这是西方用语,传统术语是声韵学)的知识。去年八、九月间疫情最严重时,我在北京隔离三周。我有很多空闲时间,才有可能仔细阅读这本书稿,重新回想以前读过的声韵学知识。所以,厉害的不只是鸿生,我也勉强算得上是一个吧(难得可以这么自我吹嘘)!
二
现在有不少人已经知道,汉语方言中保留最多唐音的,要属闽南话,在这方面,连广东话和客家话都还比不上。其实,闽南话里也保留了一些唐以前的词汇。举两个最明显的例子:
鼎
在普通话中很少人用这个字,因为这个字太古老了。“鼎”是国之重器,成语“问鼎中原”的“鼎”就是这个意思,在宗庙祭祀中,“鼎”也是重器。但在闽南话中,“鼎”(音tiánn)却是煎、煮的炊具,有大小之别,大小之间可以差别很大,不过却是最普通的炊具,也可以用来炒菜,在闽南话里是常见的词汇,一般口语都用。在普通话里,这个字极少用到。这就说明,闽南话中的“鼎”是非常古老的字,从古代一直保留到现在。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箸
在闽南话的口语中,这是个单音词,念tī,其实就是普通话中的“筷子”,而“筷子”却是双音词,这是唐宋以后才有的,以前用的是“箸”这个单音词,客家话可能还用这个词。“箸”比“筷子”古老得多。凡是现在普通话已经不用、而闽南话口语中还常用到的单音词,应该是从很早以前就保留下来的。
闽南话口语中还有一对单音词,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那就是:“行”(音kiânn)和“走”(音tsáu)。这两个词,现在的普通话改用“走”和“跑”。请看《孟子》中的一段话:
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孟子·梁惠王上》)
吕正惠《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弃甲曳兵而走”的“走”就是“跑”的意思。闽南话口语中的“走”字也是“跑”的意思,其词意和《孟子》所用的“走”字完全一样,说明闽南话口语中的“走”其词意至少可以追溯到《孟子》。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
这句话翻成现代白话,就是:“三个人在一起走,其中一定有人可以当我老师。”在这里,“三人行”的“行”字就是现在白话文“走”的意思。现在的白话说:“走,走,我们去看电影。”这句话用闽南口语来说,就是“行,行,我们去看电影。”实际上在闽南话中我们确实是这样讲的。这就证明,闽南话口语中的“行”和《论语》“三人行”的“行”是同一个意思,就等于现在白话文中的“走”字。“走”和“行”这两个例子可以证明闽南话的古老,因为其词意可以追溯到《论语》和《孟子》。
还有一个例子也很重要。有些地方的闽南话,把“书”说成“册”,把“读书”说成“读册”(我生长的地方就是这样)。很早以前,中国人是把文字写在竹简或木简上,因为每个简片写的字相当有限,一篇文章要写在很多简片上,然后再用绳子串连起来,“册”就是绳子串连两个简片的象形字。由此可见,闽南话口语中的“册”来源是非常古老的。
吕正惠《写在人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
以上所说的是,闽南话口语中来源比较古老的词汇。闽南话也有很多词汇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只是这些词汇现代白话已经不用了,所以当我们在唐代文学中看到这些词汇时,会觉得有点奇怪,不知道要怎么解释。譬如: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李白《月下独酌》)
“解”这个词,在闽南话口语中念成ē,是“晓得”、“懂得”的意思,“不解饮”其实就是“不懂得饮酒”。唐诗中的例子很容易找,譬如:
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李白《金陵城西楼月下吟》)
世人解听不解赏,长飙空中自来往。(李颀《听安万善吹筚篥歌》)
入春解作千般语,拂曙能先百鸟鸣。(王维《听百舌鸟》)
隐士休歌紫芝曲,词人解撰河清颂。(杜甫《洗兵马》)
梅祖麟《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鸿生引述梅祖麟教授的说法,认为这是南北朝至唐代口语中常用的词汇。后来的北方官话并没有这个词,而用“会”字来替代。
梅祖麟(1933~),现为美国康奈尔大学中国文学和哲学教授,专业方向为汉语语法史和汉藏语言比较研究。
闽南话还有一种常见的例子,先引述如下:
斗阵(音tàu-tīn) 结伴
斗做伙(音tàu-tsò-hué) 将两人或两物拼在一起
斗闹热(音tàu-lāu-jia̍t) 凑热闹
斗跤手(音tàu-kha-tshiú)帮忙
这种用法在宋代诗词中比较常见到,如:
春色初来,遍拆红芳千万树,流莺粉蝶斗翻飞。(晏殊《酒泉子》)
好向歌台舞榭,斗取红妆娇面。(曹冠《水调歌头.红梅》)
三分兰菊十分梅,斗合就、一枝风月。(辛弃疾《鹊桥仙.风流标格》)
双堤斗起如牛角,知是隋家万里桥。(晁补之《扬州杂咏》,按此例为诗,不是词。)
“斗”这种用法,鸿生所举的例子都是宋代作品,我在唐诗中很少看到,说明这种用法在宋代比较常见。不过,现代普通话中已经很少使用。
以上所举的闽南话口语中的实例,从最早的“鼎”、“箸”、“册”到唐宋时代的“解”(唐代常见)、“斗”(宋代常见),都可以说明,从秦汉到唐宋的某些词汇,在现在的闽南话口语中都还有所保留。鸿生引述了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对这种现象做了总结:
在一般的方言当中,一个词往往有两种或多种读法,包括文白异读。这些不同的读法反映移民及其文化浪潮的历史层次。如在厦门方言中“石”字,口语读[tsio̍h],单用,指石头;在石砚(砚台)中读[sia̍h];文读则是[si̍k]。又,“蓆”字,在“蓆仔”(草蓆或藤蓆)中读[tshio̍h];在“筵席”中读[sia̍h];文读则是[si̍k]。这两个字的三种读音,第一种应该是秦汉音,第二种是南朝音,第三种是唐宋音。这三种音代表厦门话的三个历史层次,这也正是北方文化在秦汉、西晋末和唐末三次入闽的遗迹。(此处引文重点为吕正惠所标示)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文中所使用的例子刚好足以说明,北方汉人入闽的三波潮流,第一次是汉末天下大乱(包括黄巾起义),第二次是西晋永嘉之乱,第三次是唐玄宗末年的安史之乱和唐末的黄巢起义及其后的北方战乱。三次入闽,都有当时的北方口音留存下来,前两次留在口语中,最后一次输入的是读书音。这些例子恰恰足以说明,闽南话按北方汉人入闽的三波,刚好留下三个历史层次。(本节所述内容参见本书第六章《为什么说闽南语是古汉语的活化石?》)
三
客家话、广东话和闽南话,都相对完整的保留了中古汉语(魏晋南北朝至唐代)的入声字和入声韵,但是,好像只有闽南话存留下口语和读书音两套截然分明的系统?客家话和广东话似乎并非如此?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应该加以探讨,才能说明为什么闽南话所保留的唐音最为完整。
郑鸿生《百年离乱:两岸断裂历史中的一些摸索》台社论坛2006年版
首先要谈广东话。按照中国的历史记载,秦始皇派了五十万大军征讨岭南,这是北方汉族移居广东之始,所以汉族迁移到广东,远早于闽南人和客家人。但是,现在的粤语却很少存留下古代汉语的痕迹,为什么?
鸿生对这个问题,在本书第九章《闽南语为何不像广东话那样全方位?》提供了比较明确的回答。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迁居广东的人要越过大庾岭,经由张九龄(唐玄宗朝的著名宰相,广东曲江人)所开辟的“梅关驿道”到达南雄、曲江(分别为现在的南雄市和韶关市),再散入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是一个平原区,而“广州府”(现在的广州市)则是珠江三角洲唯一的大都会,自然成为南迁汉族的认同中心,粤语很容易向广府话靠拢,所以粤语没有像闽南话的泉州腔、漳州腔、潮汕腔那样各说各的调,也不像客家话分成四县腔和海陆丰两个系统。闽南人和客家人所居多山地,各地往来不便,又不容易出现像广州那样的大都会,各地方音不容易统一。(厦门在鸦片战争后才对外开放成为港口,时间上比广州晚多了,而且厦门也缺乏像珠江三角州那么广大的腹地。至于客家人居住区,连厦门这种规模的城市都找不到。)
其次,按我个人读历史的经验,汉族迁入广东虽然比福建早,但移民真正大量迁居到广东却是在北宋末年靖康年间金朝攻陷汴京以后。(我读南宋文学史,发现南宋有不少文人住在广州,可以作为佐证。)这一大批移民带来了汴京的“官话”,这一官话系统迅即覆盖了原来广东话所存留下来的较古的汉语,古汉语几乎全部消失。这就造成一种极为特殊的后果,即,从这个时候开始,粤语就是“言、文”一致的,也就是说,口语和读书音几乎完全一致(因此现在广东话的主要来源应该是宋代以开封为中心的北方话)。这种“言、文”一致的情况,在英国殖民香港的时候有意识的加以利用,才会形成今天香港人不太愿意讲普通话、写普通话的原因。鸿生似乎很羡慕香港广东话的“全方位”使用,其实这是英国的殖民政策所造成的偏颇现象,并不值得效法。而且这也仅限于香港,整个广东省并不是这样。当然,“广府话”在广东的流行,确实让广东人不必透过普通话就可以相互沟通,这也影响了广东人学习普通话的意愿。讲客家话和闽南话的人,与其去学习对方的地方腔(譬如,闽南漳州腔去学潮汕腔,或者客家四县腔去学海陆丰),不如直接学普通话。我个人认为,这可能是客家人和闽南人普通话一般讲得比广东人好一点的原因。(这是个人的推测,不一定正确。)
客家话主要分布地
由此也可以推论,客家话口语和读书音几乎一致的情况,是比不上广东话的。鸿生和我对客家话都很陌生,我只好到处询问我的客家朋友和学生。我问他们一个问题,“你用客家话读三字经困不困难?”有一个客家学生回答说,他和家人都觉得,用客家话读三字经不觉得很困难,跟口语很近,只有里头的一些词语比较古老,读起来有点别扭。我还问一个问题,“你们用‘鼎、箸、册’这三个字吗?”有一个回答说,“箸”老一辈还用,年轻人大半不用,另外两个字已经不说了。这些都足以证明,客家话所用的古词汇比闽南话少,口语和读书音的距离没有闽南话那么大。可以说,关于口语和读书音的关系,在广东话里,两者的距离很小,在闽南话里,两者的差距很大,闽南人要学读书音,确实是需要经过一翻努力的,而客家话则介于广东话和闽南话之间。
关于客家话的历史,我看的资料不够多,不过,各种意见参差很大。有客家学者认为,客家话的形成史比闽南话早,这种说法我有点怀疑。我曾经从闽西到赣南,来回走过两次,也到过现属梅州市的好几个县。终于了解,以前从赣南进入闽西,要顺着汀江进入汀州(现在叫长汀,瞿秋白就义处),再从汀州散入闽西山区,然后沿闽西山区往南走,就可以到达梅县,从梅县往西南,就是惠州和海、陆丰。这大概就是客家人从江西迁往福建、广东的主要路线(客家人零散迁入广西、西川等地的状况就不必多说了)。这让我想起另一种关于客家人的迁移史。按照这种说法,南宋末年文天祥在江西南部起兵抗元,失败后大量赣南客家人顺着汀江往福建逃难,这才是广东、福建后来成为客家人主要居住区的原因。按照这种说法,客语的完全成型显然要比粤语和闽语晚得多。根据我两次的闽西、赣南之行,我比较相信这种说法。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从长汀往闽西走,可以看到文天祥幕客谢翱在那一带客馆教书的足迹。谢翱应该是随着赣南客家人一路往南走的。
谢翱(1249年11月20日—1295年12月17日),南宋爱国诗人,“福安三贤”之一。
客家人长期处于山区,彼此连络不便,又跟江西、福建的畬族融合,所以后来形成的客语远比粤语复杂,这是客语所保留的古语和来源不明的词语比粤语多的原因。
四
按照上一节所说,闽南话保留的唐以前的汉语,显然要比广东话和客家话多得多。跟闽南话相比,广东话和客家话保留的古汉语大都属于宋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异呢?现在我们根据前面所说,再进一步推论。
首先要谈到,经过五胡入华、南北朝大分裂以后,到了隋朝中国又复归于统一。南北朝时代,从印度和西域传来的佛教,在中国大为盛行。因为翻译佛经的关系,中国文人开始意识到,相对于梵语,汉语的特殊性就非常明显。譬如,汉语需要分声调(当时分为平、上、去、入四声),而声调在梵语中并不重要。借助于梵语,中国学者开始分析汉语的特质。所以从三国时代,中国才开始产生了研究切韵的音韵之学。
再者,北方由于大量胡人进入,同时由于北方战乱,大量汉族逃到南方,这样,南北各地的口音产生很大的差距。中国重新统一之后,隋代学者在陆法言等人综合三国以来的音韵知识,有系统的编撰了《切韵》一书,想藉由这部书呈现中国各地口音的差距。同时,又由于隋朝开始举办的科举考试,到了唐代加考诗赋,全国参加考试的读书人,必须有一套“正音”标准,也就是说,要有合乎“标准音”的押韵方式,这个时候,《切韵》就成为一部非常重要的参考书。没有这一部参考书,全国不同口音的读书人将无所适从。这一部《切韵》经过唐宋两代的不断改编,就成为中国传统典籍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书,这一部就是《广韵》。《广韵》是中国声韵学最重要的典籍,在科举考试时代没有一个读书人会不熟悉这部书的。如果不知道这本书,他起码也要常常翻读更加通俗的《平水韵》,没有这部书,在考试时你根本不知道根据什么标准来押韵。所以,正如鸿生所说,“切韵音系作为唐宋时期中原的正音标准,向四周扩散,影响到各地的方言。”在科举考试“正音”的影响下,就形成了汉语方言中非常独特的“文读”系统。
左:《切韵》;中:《广韵》;右:《平水韵》
《切韵》是隋代陆法言所著韵书,成于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分193韵。《广韵》为北宋陈彭年、丘雍所作韵书,是《切韵》最重要的增订本,分206韵,它使已经亡佚的《切韵》的古音得以完整地流传了下来,成为研究中古汉语语音的重要资料。南宋刘渊编纂的《平水韵》分106个韵部(其书今佚),是《广韵》的一种略本。
闽南话因此形成的文读系统,所以跟原有的口语系统产生很大的差距,是因为文读系统的切韵音系在唐朝末年输入福建时,闽南话原有的口语系统已经沈积了三个历史层次(第一次是东汉末北方汉族的南迁,第二次是永嘉之乱,第三次是安史之乱)。闽南人又大都居住在各自的区域,彼此之间很少交流或迁移,这就使得他们前三次所带来的北方汉语很多都能保留下来。到了唐末黄巢之乱时,河南固始人王审知又带领一批北方人逃难进入福建,这是第四批了。王审知在福建建立“闽国”(五代十国之一),非常重视文教,在各地普遍设立学校,还举办科举考试,当时福建诗人之多在五代时期是有数的,这样就为福建的文读系统扎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福建同时存在口语和文读两个系统,然后两个系统“文、白”融合,使得闽南话更形复杂,成为汉语中最为独特的方言,为其他方言所不及。(这是我讲话的口气,鸿生比较慎重,不会讲得这么肯定。)
王审知兄弟入闽路线
有了闽南话作为对照,我们就比较容易解释广东话和客家话的文读和口语为什么没有闽南话那么截然分明。前面已经说过,大量汉族移居到广东,最重要的一次是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乱;大量汉族移居到闽西和粤东(以广东梅县为中心),是在南宋末年文天祥抗元失败后。这并不是说,在此之前广东和福建并没有累积一些广东话和客家话的因素,只是其基础并没有闽南话那么雄厚,所以当更多的北方人迁移到珠江三角洲、福建西部山区和粤东梅县地区时,因其数量更多,他们所带来的中原的“正音”就淹盖了早期留下的、根基比较浅薄的因素,所以才会造成后来迁入的北方正音系统(这是以宋音为主,而不是唐音)会成为广东话和客家话的主流。相对来讲,他们文、白异读的现象,就要比闽南话单纯得多。
就在粤语和客语在广东和福建地区完全确立以后,中国北方的汉语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原因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女真人和蒙古人陆续进入中原地区。女真人建立的金朝,统治地区到达淮河,包括整个中国北方;而蒙古人则统一了全中国,建立了元朝。从此以后,北京就取代了长安、洛阳、开封(汴京),成为北方的文化中心,然后,以北京为中心,历经金、元、明、清四朝,至少七百年期间,逐渐形成了北方官话系统,并在这个系统之上形成了现在的普通话和白话文。
闽国(浅绿部分)
北方官话和白话文对汉语最大的改变,就是入声字最后完全消失,以唐诗宋词为核心的中古时代诗词的音韵效果在普通话中很难完全表现出来,而南方最重要的三种汉语方言,则保留了中古的入声字和入声韵。这样的汉语知识,几乎为官话系统的人所忘记。这当然是历史变化的结果,人力难以挽回。(这也是女真人——包括金代和清代的女真人、以及蒙古人,和汉族相融合所产生的结果。)这是我们谈论广东话、客家话,特别是闽南话的历史时,必须记得的事情。而台湾讲闽南话的人,对此完全不具备历史认识,反而把闽南话当成“台湾话”,然后把他们所谓的“台湾话”和“中国话”(或“北京话”、或者“中国普通话”)完全对立起来,认为是两种完全不相干的语言,天下还有比这个更荒唐的“知识”吗?
由此可知,鸿生的书,是一本追本溯源的书,是台湾的闽南人追寻自己文化根源的书。为此,鸿生花了很多时间阅读中国历史和中国语音学史的资料,并且还整理成一本书。这不是一般的读书笔记,而是“有为”之作,虽然不是很好读,但我们绝对不能忘记他的“良苦用心”。
2022年8月20日
补记
鸿生这本书,花了许多篇幅谈论闽南语音韵系统的变化,这方面的知识非常专门。我在正文中夸称我的声韵学学得有多好,但是要把音韵系统的变化“科普化”,还是力有未及,只好请请鸿生和读者原谅。
我的序言主要集中讨论闽南话中所包含的复杂的词汇现象,以及因此而涉及的文、白异读问题,主要想让读者略微了解闽南语词汇的历史变化,并由此体会闽南语蕴含了不少古汉语现象,在现代汉语方言中是最为特殊的。
我本来还想谈两个问题。第一,现在世界上的主要语言,都采用拼音文字,只有汉语不是。对汉语来讲,汉字的重要性绝对不下于音韵系统的变化。从甲骨文到现在大陆通用的简体字,汉字字形虽然不断变化,但我们应用起来仍然没有什么困难。汉字的不变性,让我们不必花太多心血就能了解古籍的文字。可是,拼音系统的字并非如此。因为拼音系统的文字,会随着声音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譬如,十四世纪的英语就可以算古英语了,除非是学有专长的专家,一般人是很难阅读的。而汉字所记载的公元前四、五世纪以降的典籍,如《诗经》、《论语》、《孟子》,对我们来讲,大半都还可读懂。也就是说,以字形为主的汉语、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在长期维持汉文明的统一性方面贡献非常的大,这一点常为人所忽略。比起拼音文字,汉字学起来确实困难得多,但在传承典籍方面,汉字的功能远远大于拼音文字。晚清以降,不少人认为,汉字严重妨碍了中国人识字率的提升和知识的普及。这种认识其实是大有问题的。对汉字的功能问题,我们必须客观的重新评估。
其次,要谈到汉字与《切韵》音系的关系。因为有了汉字,中国音韵学比起其他文明,好像要落后得多,所以,中国第一部韵书《切韵》居然晚至公元七世纪才出现。但是,《切韵》音系确实能够反映汉语各地方音的差异。当全国举办统一的科举考试时,《切韵》音系反而可以提供一套准则,让不同方音的人容易向政治、文化中心靠拢,重而产生“正音”作用。这就使得各地汉语虽然南腔北调,但当中国人感觉到,国家有必要更加团结时,一种为大家所接受的“通用语”(如现在的普通话、即台湾所谓国语)就很容易得到推广。在台湾,本地人大都不喜欢国民党政权,但国民党所推行的国语却大为成功,连“台独”派都不得不使用,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以上这两点都还可以详尽发挥,但这篇序已经够长了,只能以后再补写了。
又记:本文初稿承鸿生仔细修订,提出修改建议,并代为注上闽南语音标,非常感谢。
「 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